《人物》小说课优秀作品:像那辆列车一样远去
我们相信,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可以写出一篇绝妙精彩的小说。两个月前,《人物》联合双雪涛、笛安、郝景芳三位优秀青年小说家打造了写作课——《像小说家一样写作》,在36天的课程后,小说家挑选出了部分作业并作出点评。笛安在回复中写道,“其实我收到的所有作业,总体水准都已超出了我的预期,大家很棒”。
以下就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小说选登:
文|谢大脚
上篇
今天,雨,摄氏18~23度。慈余的公路像一条流入大海的河。
披上雨衣,我骑着自行车去了邮政所。她开始向我要钱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许爱她。「刚开始」这三个词总是美好的,不像癌症晚期的恶化已无可救药。我想我现在应该还是爱她的,否则我就不会去给她寄钱了。雨水顺着车衣的帽檐滑落下来,四周只有雨滴敲打万物的声响。
其实不过是一千五百块钱,但我突然想离开柜台就这样算了。那样我们就真的结束了,甚至不需要任何通知。1997年,我十八岁,在南方当兵。为了买一块西铁城的手表,骗家里人在军队生了病,寄了五百块钱,偷偷买下。后来我退伍回家,遇上隔壁邻居吵架,当时狂气重,一言不发冲上去给人兜脸一拳。手表正好磕到对方的眉骨,玻璃碎了,指针不再走动。我大概并非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为此难过了几天。谈朋友不是买表,感情碎了连尸体都找不到。死人还有墓碑凭吊,胎死腹中的爱连无名冢都配不上。
仔细算算我们才认识了九个月,且四个月前她就回老家了。我想我不该告诉她我家祖上是大户人家。我怎么把爷爷辈的事情也翻出来吹牛了呢?我说我爷爷原先是大地主,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表情如故,假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我说,真的,没骗你,现在我家旁边那一圈地原先都是我家的大宅院,我屋后面的小杨一家,就是以前给我家看宅子的。她身子侧过来一点,嘴巴里呼出的热气喷到我脖子上,痒丝丝的,那侬家里还有古董没有?她学本地人说土话,说来说去也只会港「侬」、「阿拉」、「好伐」这几个字,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可爱。我说,早没了,抄家还不得抄光,留一件都是要人命的事情。她意兴阑珊地说,那侬港色系(什么)。我笑了,这句倒讲得蛮本地人。我叫她把头靠过来,在她耳边悄悄地说,其实还藏了一个青花坛子,明代的。她咯咯得笑了,说,阿拉家以前也是大地主,按理说我也是个小姐呢。我说,正好,小姐配少爷天生一对。我俩被逗得不行,在长椅上捂着肚子笑个没完,最后我先牵住了她的手,她用指甲在我的手心不停画圆圈。指尖凉得像一片融化的雪。
我家真的有一个明代的古董坛子,不过在我小时候就被摔碎了,坛口磕掉了一大块,腌榨菜芯子都嫌寒碜。事实上就算没破也值不了几个钱。而我家的大宅院,在我出生前已经拆得连影子都不剩了。我还是把钱寄给了她,就当做是那句话的补偿。还不还都无所谓。事实上她当时并不只是向我借钱。她在电话里说,我俩不合适,如果没有隔着一千多公里或许还能再试试,总之就是那些话。分手的理由都得足够冠冕堂皇,好像不这样就跟牲畜交配似的。她最后才提借钱的事情,她说借不借都行,她都拿我当朋友看。我心想借了也没啥好事,那我干嘛借你?你还要跟我分手,我这不当傻逼吗。但为了证明我比她体面,我丝毫没犹豫就答应了,好像我家真的有个完整无缺的古董坛子。
有那么几次,我想告诉她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如果她跟我在一起,我父母也没什么能给我,而我可能连一个装有自来水管的家都给不了她。夏天,她要一桶一桶地接井水洗澡,还得忍受偶尔有几只鸭抢先在桶里拉屎。冬天,她要在清晨砸开水缸里厚厚的冰层,取天露水洗脸。富贵之地也生产穷人。我从出生就住在这里,但没有一块黄金是属于我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我比谁都明白。如果我们结婚,总有一天会互相举着菜刀对峙,等到那一天,她会质问我那口青花坛子埋在哪个角落,我会逼她把刚开始谈恋爱时的女孩交出来。或许某一刻菜刀会迎头劈下,或许我们举累了就放下了。生活从此静如死水。
当她还在这座城市寻找财富的时候,她有份工作是招待所的服务员,偶尔打扫打扫客房。忙里偷闲时还能用房间里的电话找我聊会儿天。她曾经在客人退房后清理床单时,抖出一条金手链。我们在公园里讨论怎么处理这笔不义之财,她不敢戴在手上,怕被发现,最后决定由我卖掉换钱。她问我,是不是不太好?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们还是把它还回去,现在我就去金楼给你买一条属于你自己的?除了握住她的手告诉她谁捡到就是谁的,我什么都说不出。我不知道她拿这笔钱去做了什么,不过女孩子花钱天经地义。
招待所附近就是影剧院,我不清楚它在那里多久了。没有哪栋建筑比它的功能更多了,又是礼堂,又是文艺表演舞台,转头领导又在那里开会,偶尔还放放电影。我带她去那里看过电影,票是厂里发的,几百人的礼堂几乎全是熟人。电影放到一半,我想起谁说以前生产队开会就去大礼堂。我突然感到恐慌,也许银幕的位置从前有过一排凳子,一排人,一排高高的帽子,现在都成了漂浮的游魂在空旷的礼堂里。其实没有根据,或许那时还没造影剧院。不管怎么样,一切都过去了。2003年某个春天的夜晚,我和我的女朋友坐在这片古老的遗迹里看电影,周围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狂笑。
我把打瞌睡的她摇醒,说,口水流出来了。她小巧的手腕滑过嘴角,我猜是鱼的触感。她白我一眼说,小骗子,电影放完了?我说,我想亲你一下,你同意吗?她摇摇头说,不同意。我失落地将目光移向从二楼放映室投下的那束光,尘埃在光里飞扬。当她把嘴唇凑上来的瞬间,我明白了光不仅有形状。光像一个吻般美妙。她说,傻逼,只有我能亲你。我说,你再叫我一次。她的眼睛亮晶晶的,说,傻逼。还没说完我就吻上了她的嘴。傻逼。一个吻。傻逼。一个吻。我说,你还叫不叫了?她特坚定地说,大傻逼,你亲死我吧。说完自己就乐了。我也笑了。
电影散场后我们又偷偷从窗户爬了进来。影剧院的窗帘积攒着厚厚的灰尘,不知能上溯到哪年哪月。使劲吸口气进去,我怀疑霉斑会移植到肺里。快到高潮的时候她幽幽地叹了口气,我停下来问她怎么了。她的小手缠在我的脖子上,一片漆黑中我感觉到了她睫毛上的水汽。她说,为什么屋顶不是透明的,这样我们就能躺在地上看星星了。我突然灵光一闪,说,你等一等。我从旁边的衣服里摸出一盒东西。一团火升起来,点燃了她的脸,在空中滑过后又暗了下去。她的身体像月光下浮出海面的蓝鲸,耀眼过后又沉入水底。一根根火柴像流星一样坠落。我们像宇宙深处两颗遥遥相望的星球。最后一根火柴燃尽的时候,我说,好了,你可以安心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烟火味。她的眼泪也是呛人的。
或许我应该留住她的,她是一个好女孩。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让她走。但我没理由拦住她回家奔丧。我也没理由逼着她回来。
或许哪天我应该去找她。
下篇
我没有骗他,我真的有机会成为大户人家的千金。
我的外公是村里最大的地主,连着被土匪抢了三次。最后一次的时候,有人来村里通风报信,说土匪快要来了。外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装进三个箱子,叫了几个小工准备抬到山上去。那几乎是外公所有的家产。都说无巧不成书,造化弄人,谁能斗得过天?请来的小工还没来得及抬箱子,土匪先进了村。我妈妈是家里唯一没出嫁的女儿,她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嫁妆被抢走的。解放后,三年饥荒,外公只能吃糠,肚子硬的像充气的皮球,拉不出屎死了。我一直在想外公死那么早是不想看到我妈受苦。如果有时光机的话,我会用生命做赌注跟时间赛跑,我要回到那一年之前,告诉她,妈妈,妈妈,你快点结婚吧。也许我会像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凋谢了,但妈妈一定会过得幸福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他以为我也许爱他的钱。可我知道他没有钱。什么古董坛子,不过都是跟外公的宝箱一样烟消云散罢了。但我不能说破。我现在不在乎,但我没法保证等到将来我们一起生活时,某次激烈的争吵后我不会拿它说事。也许我会痛骂他是一个骗子,一个穷鬼,即使我在嫁给他时心知肚明。当那对小夫妻第二次来招待所找金链子时,看到那个女人委屈得想哭的脸,我是发自内心得想把手链还给他们。但我不能。它已经被我在打金店换成了我妈的救命钱。他们一定还会有第二条金链子,但我没有第二个妈妈。我想告诉他们等我将来赚到钱后一定会加倍的偿还他们。但我不能。我保证不了任何事情。
在人生进程中的某几个结点,将会因为我们的选择而导致生活与之前截然不同。我自以为是地做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抉择,人生并没有因此好转。我不得不怀疑我的人生是一个错误。对我而言,某一个瞬间明确地改变过我。
这「一瞬间」发生在2002年11月27日。那天他告诉我,他年少时在南方当兵,每次回家习惯坐晚上十一点五十八分的到上海的火车,再从上海转火车到县城,再一路颠簸地坐公交回家,正好赶上午饭。我想象他在午夜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轻轻点上一支烟,同那些亡命天涯的陌生人共处一室,好似穷途末路的孤胆英雄。我没办法形容这种感觉,但我确实被打动了。小时候,我家在山里。有次夏天的晚上,我和姐姐睡在露天阳台上,远处起伏的山脉融在夜色里像蝾螈黑色的背。我们凭肉眼看到了银河,像一条粉末铺成的腰带,镶在密度极大的星群里。作为背卧大地的生灵,包裹在天地的浩渺里,我们在这种感动中紧紧握住彼此的手未发一语。我相信这种感动只能被自身知晓,无法诉说与分享。我爱上他,就像爱上那夜的星空,来自于对个体的同情和极致的浪漫。
我们合伙干过很多傻逼事。我提议我俩各自带对方去一次平常去不了的厕所。他先带我去了公园男厕。进去前,他意味深长地说,你可别给我斗鸡眼哪哪都不敢看,丢人。我咬牙切齿道,就你废话多。其实我在里面待了几秒就出来了,原先我还计划撒泡尿再走的。但后来我死活都不肯带他去女厕。他骂我骗子。我说,骗子配下流胚,半斤八两。吵着吵着我们就像两只树懒一样抱在一起接起吻来。
公园的一切都是免费的,甚至连小动物园都不需要门票。小动物园坐落在公园的东南角,入口是一个大铁硼,七七八八地放着半死不活的微型盆栽。我们在里面「养」了一只骆驼。每次我们来喂它的时候,它都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望着我。我可真受不了,那双眼睛衔着一片汪洋大海好像在问我沙漠在哪里。骆驼呀骆驼,咱俩都是外来客,我也想念我的沙漠啊。那时候,我觉得我和骆驼才像是一对,有些事情他根本理解不了。
我也许真的爱他。后来,我变得有点不愿意离开他。如果那时他陪我一起踏上火车的话,我就会在心里承诺他,我可以为他背井离乡。葬了我妈以后,我还是想立刻回到他身边。但我不能。他不知道我家是什么样子。我俩通电话的时候,我会想象要是他来到这里。地下一层的菜市场被昏黄的灯光照得像鬼城,到处浮动着呛鼻的辣椒粉,阴雨天里污水沿着台阶蜿蜒而下。夜晚的山里死一般的寂静,文明的触手路灯还未伸向这里。他走在山崖边,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拿着长竹竿,驱赶道路两边成排的四脚蛇。他终于来到我的小屋前,借宿在通过梯子抵达的阁楼,像小动物一样匍匐前进。晨起被隔壁猪圈里的咕噜咕噜声惊醒,在猪屎牛屎羊屎的粪便味里辨别身处何方。或许他会一脸坏笑地说,你家可真热闹。要不然就含情脉脉地告诉我,他一定会照顾好我。算了吧,哪一种口吻我都接受不了。总有一天我们会没那么相爱,总有一天那张说出过无数情话的嘴会冷笑一声,不屑地嘲讽道你别忘了是谁把你从一堆屎中拯救出来。我会连回击的话都找不到的。我留下的时间越久,我就越不能到他身边。
真难过呀,我有什么选择呢?就算我能凭我这张脸得到一份清闲的工作,每天重复「你好」、「再见」之类的客套话。直到某一天傻逼主管叫我去复印一份文件,我这个不识字的前台小姐在马路边手足无措了半天。最后绝望地打电话给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复印。我想这话应该是带点哭腔了,真丢人,我哭着跟他说我后悔小学没毕业了。他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说,二,你他妈真是个混蛋。他说,够了够了,对我来说你这样就够了。我字正腔圆地骂他,侬咋噶伐识相。但是我抓住那只伸过来的手了,即使这份勇气片刻后就烟消云散。
可是对这个世界来说我还是一个不合格的人,不然就不会年纪轻轻在招待所里伺候别人了。在没认识他之前,我每时每刻都希望遇到位从天而降的台湾富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这个人带我走就好。我曾经就是这样的渴望不劳而获。
四个月了,他还是没勇气承担我反悔的后果。我不想当一只养在小铁笼里的骆驼,每天等着别人来喂草。最初,我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迟归期。我告诉他,葬礼办完了,但我得处理剩下的事情。好不容易回家我想多休息几天。腊肉太好吃了舍不得回来。家里的猪要生崽了头胎容易难产我得守着它。后来就不需要借口了,好像我留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傻逼,如果他借我钱,我一定不会还给他。我就要他急得跳脚。我就让他以为我是一个分手了也要骗他钱的女孩。也许那样他就会追过来,跟我再唇枪舌战一番。
或许他不会给我打钱。钱不是问题,答案才是。其实答案也不是,勇气才是。只能他先迈出这一步。谁也不能保证这场游戏不会输,我不想连筹码都丢掉。
或许哪天他会来找我。
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最好的结局。或许哪个都不是。但总有尘埃落定的一天,像那辆载着他开往上海的火车,迎来送往,一切都会过去的。
本文为人物【像小说家一样写作】系列课程笛安学员优秀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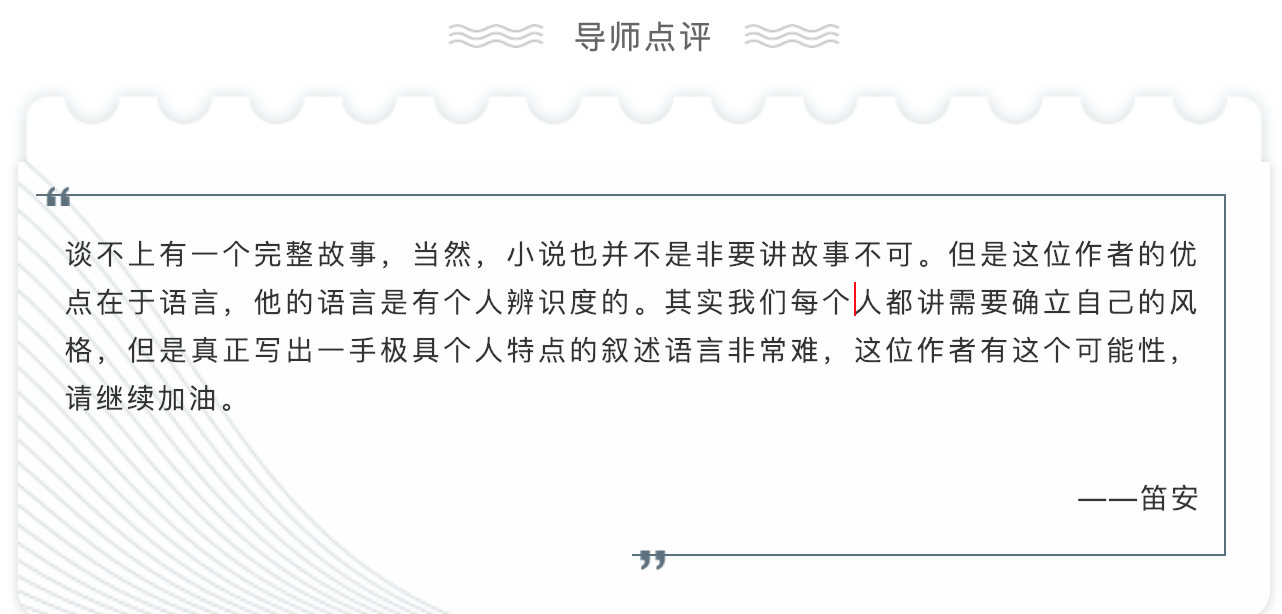
TOP STORIES
相 关 推 荐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