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们,音乐是你们的解药

本周末,我们分享的是病人们的生活意见。指挥家小泽征尔在本月初向全球直播了自己的一场小型音乐会,坂本龙一先生也将有一场钢琴演奏会,就在这个周日。也许,它们对此刻的你并不重要,你应该关心更具体的生活,有没有足够的蔬菜,能不能保证正常的睡眠,是否能够保护自己不要生病,关心自己在乎的人,照料他们的健康。在这个冬天,音乐是不怎么顶用的奢侈品,当你因为高烧而辗转难眠,把贝多芬播放一万遍也不能好起来,能真正治愈你的是布洛芬。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这些音乐家。举办音乐会的时候,小泽征尔病到根本不能走路,坂本龙一的演出是在他确诊癌症四期之后作出的决定。他们也应当活在更现实的生活里,听从医嘱,静养休息,去照料自己的病。可是他们却决定,从具体的生活里抽离出来,回到音乐里。这些不听话的病人究竟在音乐里得到了什么?这是今天的文章想要解答的谜题——为什么音乐大于了他们的具体生活?为什么对这些病人而言,音乐似乎成为了他们的药?
这就是本周末的生活意见,它来自一群音乐病人,对他们来说,交织的旋律不只是一种人生的奢侈品,不只是平安无事时的消遣,它是一种力量,超越了衰老,超越了晚期癌症,成了一种足以让他们活下去的解药。也许他们的答案未见得能帮助你解决此刻的生活难题,但至少它们可以给我们一点力量,在困顿的日子里打起精神——因为明天有坂本龙一的音乐会。
周末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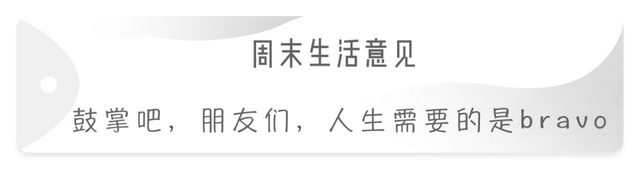
文|查非
指挥家小泽征尔不用指挥棒,一切音乐讯号都来自他的手势,握紧的拳头表示强奏,手臂挥舞的幅度越大,渐强的声音就要越响亮。他还有一个极少使用的专属手势——两个食指同时弯成环,台下的工作人员就要赶紧冲上台,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这是他们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代表SOS,「我不行了,快来救我」。
小泽征尔今年87岁,12年前罹患食道癌,此后的他是一个病人,病了去医院,出院没多久就去彩排,台上病倒了再去治疗,恢复之后又要回舞台,这就是小泽征尔十多年间的生活。医生看过他的检查结果后跟他说,他不应当继续工作,但是,他还是坚持回到舞台,指挥音乐,直到今天。

1982年10月8日,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彩排期间的小泽征尔。图源视觉中国
最近一次的音乐会发生在2022年12月1日,听众只有一个人,是一个远在国际空间站的日本宇航员。小泽征尔选择了自己年轻时最出彩的作品之一,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指挥台上撤掉了放曲谱的架子,腾出空间放他的轮椅。乐手们多是跟他共事数十年的老朋友,全都集中精力注意指挥的手势。他坐在轮椅上,胳膊挥动不起来,好在肩膀还有一点点活动空间,稍稍抬起手臂,他用眼神给了乐团一个讯号,音乐开始。
指挥台上的小泽征尔,像一个不听话、总想跑出去玩的孩子,一点点试探生命的边界。宣布自己患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的发言要点有两条,第一,自己罹患食道癌,即将接受食道切除手术;第二,他会很快回到舞台,半年内一定回来演出。其实术后还没到半年,他就已经恢复了彩排。一开始他想指挥全场音乐会,彩排中途他就开始想吐,不得不停下来。他在术后体重骤降15公斤,体力下降,每走六步路就需要坐下来歇一歇。后来他试着把曲目时长缩短在一小时之内,走出排练厅就已经呼吸不畅,再后来,曲目缩减到半小时以内,因为胳膊渐渐抬不起来,无法指示渐强讯号,彩排时只能苦笑,用左手捏捏右手,「动不了啊!」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他没有完整指挥过一场音乐会,但他总是要回来,像是一种执念,一定要回到音乐里去。最短的一次,他只上台指挥了三分半钟。全场响起此起彼伏的Bravo,小泽征尔在后台和周围的人告别,「现在我要去医院了。」
生病的小泽征尔成为了古典音乐世界里最出名的跳票指挥家。答应了要去指挥,彩排中途累倒了,不得不临时换人执棒;承诺要参加音乐节,开幕前一天住进了医院;预告了和钢琴家内田光子合作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临演前又再度搁置。他常常在演出前一天甚至演出当天告病缺席,以至于有时音乐会根本无人指挥。与他相关的音乐新闻形成了一种标准句式,「小泽征尔因____缺席演出」,这个空白处的常见词是肺炎、脱水、感冒、发烧、体力透支、骨折、主动脉瓣狭窄……
小泽征尔的事务所发布消息说,自2010年食道癌手术之后,他从来没有彻底恢复过,每次公演之后都伴发新的疾病,一直在大大小小的治疗过程中。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已不需要医生来宣告,他越来越瘦,走路距离越来越短,声音越来越小,不懂医学的人也看得出来,这个人不应当再出现在指挥台上了,如果他想要活下去的话。可是在音乐节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的表态几乎像一种恳求:「我想要指挥啊,请让我指挥吧!」
发生在小泽征尔身上的执拗像一个谜,然而,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谜。这个周日,坂本龙一将举办一场音乐会,他要回到钢琴前,再次弹琴给所有人听。问题是,和指挥家一样,此刻的坂本龙一也不应该做这件事。
2014年,坂本龙一确诊罹患咽喉癌,2020年确诊直肠癌,经过治疗后,检查发现癌细胞已转移到肝脏、淋巴和双肺,正式确诊癌症第四期。在过去两年里,他接受了大大小小总计六次手术,其中一次手术长达20个小时。尽管医生已经尽力通过外科手术切除肉眼可见的肿瘤,检查结果中依然发现了不断增殖的癌细胞。摆在他面前的唯一出路是无止境的化疗,四期病人有很多具体的事情需要考虑,即将到来的癌痛、无法预测的癌细胞转移、身体防御机制下降而随时可能发生的感染,对四期病人来说,任何一次微小的创伤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他应该静养、休息,尽可能减少外出,避免劳累。但他却做出了和这些要求相反的决定,他要工作,他开始忙碌起来,准备一场音乐会。
连他自己都知道,这是一场赌上性命的演出。在宣布此次音乐会的文章里,坂本龙一这样写道:「我已经没有足够体力来举办现场音乐会,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以这种形式演奏。」
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也不是不懂得休养,不爱惜生命。坂本龙一编曲的电脑里放着他的核磁共振结果,他时常拿出来看看。他是一个认真的病人,仔细阅读过很多癌症相关的书,对自己的病有详尽的治疗计划,在日记本上记录每天的感受,非常小心地准备饮食,每餐协调蔬菜和蛋白质比例,每天慢跑、拉伸、做力量训练,运动时间不短于30分钟。每一次的复诊检查都按时完成,认真吃药。
但是,他也活得像一个谜,总是不由自主地做出违背医嘱的矛盾选择。他清楚地知道癌症治疗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应当尽可能避免感冒,但是听到外面有雨声,他顶着一个桶就出去了,站在院子里淋雨,理由是,想听听雨滴落在水桶上的声音。癌症治疗刚刚进入维持期,突然接到导演伊纳里图的电话,邀请他第二天飞去洛杉矶,为电影《荒野猎人》配乐。他的反应记录在自己的纪录片里:只犹豫了一下,只模糊地预估自己的体力不够,但他还是答应了,理由依旧是,想要和喜欢的导演合作,想创造新的音乐。
自生病以来,坂本龙一的工作量完全不像一个癌症病人。生病的他发行了专辑《async》,办过一场音乐装置展览,为专栏撰写连载文章,和杂志总编辑对谈集结成一本书,疫情期间在现场举办音乐会,他还预告了新的工作成果——2023年1月17日,自己71岁那一天,他要发布新专辑《12》,里面是他在癌症复发的这两年所写的歌。

2018年,坂本龙一参加第68届柏林电影节。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谜一样的人物在音乐的世界周而复始地出现。贝多芬的耳聋越来越严重,他写的作品越来越多。巴托克临终病危,医生通知他紧急住院,他跟医生谈条件,请再给我一天时间,《第三钢琴协奏曲》还剩17个小节就能完成了,他告诉医生,这是他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可是,生命的头等大事不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巴托克需要的是青霉素,坂本龙一需要化疗,小泽征尔需要的是休息,他们所有人需要的都是停下来,可他们却像着了魔一样,一次次回到音乐中。不同时代的人循环跳进同一个怪圈:疾病是人生最具体、最残忍、最难以磨灭的痛苦,为什么他们总是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
看到直播音乐会里的小泽征尔,我想起了一则希腊神话故事。黄永玉把它写进了自己的诗里,主人公是一个小牧童,他能唱出很好听的歌,后来阿波罗知道了,两个人打赌,比赛谁的歌声更好听。天真的小牧童答应了,可所有人都知道,掌管天庭的阿波罗怎么会输?小牧童输了比赛,失败者被剥了皮。在画家写的诗里,被打败的小牧童奄奄一息,可是,人们凑近他时发现,他还在唱着歌。是的,小牧童输得一败涂地,声音微弱,但他仍在唱歌。
指挥台上的小泽征尔或许真的输了,一切都在离他远去。起初是胳膊,能挥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到现在只能稍稍抬起手臂,他不再能站起来,走路也是好久之前做得到的事了。围绕他的是越来越多的杂音,抱怨他总是退票,质疑他为什么不彻底隐退,还有刊登在八卦杂志上的新闻,说他病情加重,必须接受24小时照护,可是负责照顾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各有各的想法,妻子想要关闭他的事务所,儿子想让父亲见证自己的新婚,女儿反对,坚持带着父亲出去工作。三个人围站在他的病床前,互相指责,大声争论他的财产分配协议。病床上的小泽征尔看着身边的这一幕,一言不发。
他一直沉默,不再发声,直到他回到自己的音乐里。今天的演出必须坐在轮椅上完成了。音乐厅里的人在说话,但他听不清楚。每个人的脸都变得模模糊糊的。稍稍抬高一点的右手带动着左手,以最微弱的方式给乐团信号,所有乐器立即听从他的命令,音乐开始。指示乐曲渐强的时候,他根本用不上劲,着急地用脚踩着地板,想握紧拳头,手指却不听使唤。年轻时他以张扬的表现力出名,指挥强音的时候总是使劲挥舞胳膊,有次不小心撞上讲坛,生生折断了一根手指。但现在,他的力量只残存在指尖。他的处境就像是贝多芬晚年告诉医生的话,那是一句亨德尔在《弥赛亚》里写的歌词:「如果有能治疗我的医生,『他的名字应该是奇迹』。」
但是,奇迹发生了。小泽征尔病了,但他的音乐还在。残存的力量从他的指尖传递给乐团,带回了雷鸣般的旋律。《艾格蒙特》是贝多芬写给歌德戏剧的曲子,剧本讲述了一个英雄的牺牲。这是贝多芬英雄风格的最后一部作品。歌德要求在艾格蒙特被处死的结尾处,写一首《胜利交响曲》。所以,贝多芬在这首曲子里诠释了一种新的英雄,他的死亡不是一个悲剧的结尾,而是一个新的开始,音乐里有巨大的前进动力,不断指向前方,是对自由、解放、改变的预言。这是剧作家和作曲家共同的信念。所有声音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响彻音乐厅的是小泽征尔的诠释,贝多芬的信念在音乐里再次复活,英雄回来了。
小泽征尔年轻时指挥《艾格蒙特》序曲通常会在8分50秒内完成,这一次,他的指挥花了整整十分钟,但生病的小泽征尔给这十分钟填满了力量。在面向全世界的网络直播中,所有观众都见证了一个病人的顽强,他的手指只能给出微弱的指示,但他的眼睛里还有力量。音乐渐强进入最高潮时,所有声音共鸣,老人流泪了。
声音一起响起来,这种共鸣是音乐打动人心的地方。这是一个柏林爱乐乐团的小提琴家告诉我的道理。声音以每秒钟340米的速度在空气中传播,坐在舞台最远两端的乐手相隔30米,即便每个人坐得紧挨着,音符从一头传到另一头也花掉了十分之一秒,抵达耳朵的时候已经晚了,万一碰上速度标记为♩=120的快板,每一拍就占去0.5秒,所以,一群人坐在一起,创造一个声音共鸣本就是难事,而交响乐让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实现的旋律交织,抵达完美,那种感受真的接近于奇迹。
同样的共鸣感很多人跟我讲过,马友友讲过,西蒙·拉特讲过,莫里康内最喜欢自己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他在结尾写出了不同人群的大合唱。所有声音一起响起来的那个瞬间,充满魔力,就是这种力量把他们留在了音乐里。小泽征尔在癌症术后复出的排练时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那种在声音里和所有人羁绊在一起的感觉,对他来说就是活着。
坐在钢琴前,坂本龙一讲述过他的音乐理想。在纪录片中,他的手指敲击琴键,弹出了一个音,「钢琴的声音是无法长久保持的」,声音在空气中响起来,随即渐渐变弱,最终被外在的杂音淹没,完全消失,「可能我一直在追求不会消失的声音,永不衰减的声音……如果用文学隐喻来表达的话,这就是所谓的永恒吧。」为此他每天都在努力作曲,他的目标是「100年后人们还会听的音乐」。他清楚地知道,任何声音都会在传播中衰减进入无声,唯一长存的办法就是留下回声,产生共鸣。把声音传递给另一个人,它就不会消失。
这也是贝多芬写在音乐里的答案。他的人生谈不上快乐,少有亲情,没有爱情,常常为出版受阻烦恼,又罹患耳疾,很长时间活在压抑里,但是他拒绝将其定义为悲剧。他曾经告诉歌德,像他这样的人,需要的是掌声,不是眼泪。他用自己一生的作品赞美英雄,在创作《第五交响曲》的时候,作曲家描述了一个强者的英雄和几乎压倒性的命运斗争。但他的英雄理念在晚期作品中颠覆了。《第九交响曲》雷鸣般地否定了英雄的答案,上帝不会来了,祈祷没有奏效,平安不会从天而降,悲剧终将发生,战争粉碎了和平,毁灭了原有曲式。晚年的他相信另一种英雄,不必是强者,他可以活在每个人身上,他在贝九的最后写下的是合唱的《欢乐颂》,是人与人的声音共鸣。另一份曲谱上更鲜明地写着他的最后回答,「人啊,帮助你自己!」
垂死临终前,他在病床上用拉丁语宣告了自己的死亡,「鼓掌吧,朋友,喜剧结束了。」(Plaudite, amici, comoedia finita est.)
这种共鸣在很多人身上留下回响。黄永玉喜欢听着贝多芬画画,医生开的医嘱要求「静养」,但他耳朵不好,听音乐要把声音旋钮旋到最大,鼓声响起来的时候花瓶里的水都震出了波纹,贝多芬的交响乐响起来,黄永玉就要画画了。

黄永玉 尹夕远 摄
过99岁生日之前,他病了一场,因为那一天他想要画一幅大画,大幅画纸铺满了地板,他开心忙碌起来,调颜色,弯腰俯身去勾勒新的线条,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人的体力。他的家人着急地大声劝阻,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不能好好休息?
后来我见到了他,刚刚病愈的老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衰弱,摊开手,「我想画大画,画纸铺开了,我就想多画了一点……哎!谁知道多一点也不行。」我问他,画画的时候,还有画完的那一刻,开心吗?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小牧童想起了自己的歌。「开心啊!我一直想画这么一幅画,画出来了真开心。」生病的懊恼、沮丧、不甘心全都忘了,他回到了快乐里,开始分享自己的新作品,一张藏着讲不完的巧思的画作。
小泽征尔顺利完成了最近的演出,十分钟的《艾格蒙特》序曲圆满完成。在演出结束后,他有一小段时间的出神。周围的人都在冲着镜头挥手,跟远在太空的宇航员打招呼。乐手们为他鼓掌,小孩子坐在他旁边,所有目光聚集在他身上,主持人请他为大家讲句话,但是他停住了。刚刚结束的音乐演奏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他全程没有看谱,几乎是靠自己的本能记忆完成了指挥。他的确是一个老人了,病得很重,做任何事情都很慢,这也是他最慢的一版《艾格蒙特》序曲,但他的音乐依然精准,每一个指挥节点都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病人和命运的较劲。疾病像是一场不平等的审判,它夺走很多东西,剥夺行走,剥夺自由,剥夺睡眠,剥夺感受,但人的神奇之处恰恰在于,总有一些东西无法夺走,疾病也做不到。女儿在他耳边大声地提醒,他才想起来对着镜头挥挥手,努力说出「谢谢」。他的声音沙哑,是一个老人的虚弱,他花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眼泪消失在皱纹的褶皱里,小泽征尔笑了。再次唱歌的小牧童得到了快乐。
这些是发生在这个冬天的小故事,但我知道,同样的故事还会周而复始地上演。小泽征尔还会再次登上指挥台,哪怕他只能用手指发出讯号。只要重新听到贝多芬的交响曲,黄永玉还会继续画画。这个周日,坂本龙一就会回到他的钢琴前,琴槌落下的那一刻,音乐又要开始了。
人生难免有穷途末路的那一天,但或许不必害怕,末路上的人也有力量,被命运剥了皮也要高歌。这是写在希腊神话里流传了数千年的真理:在这人世间,阿波罗想要的是赢,但自始至终,小牧童只想唱歌。挨了打,剥了皮,只剩最后一口气,小牧童始终是小牧童,在地狱里也要唱歌。


人们在等待音乐会的开始 图源摄影师Stephan Rabold/柏林爱乐乐团
TOP STORIES
相 关 推 荐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