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博,优等生和荒谬感

在脱口秀的世界里,庞博像一个优等生。他收获了队友的夸赞:「优秀、帅、亲和力、韧性足、脱口秀优等生、始终昂扬、放松、真诚、喜剧斯坦尼康」,这也是很多观众对他的印象,从小到大,庞博都是一个优等生,他不出错,直面问题,目标明确。当这些特质进入脱口秀,正如媒体人肖浑对庞博的观察,他的段子,几乎都是建立在他的高智商和细致观察之上,「没有切肤之痛,于是就显得有点冷。他能共情别人,但我们普通人其实很难共情他这种天之骄子。我们就只能不痛不痒地远远欣赏着,得出一个这人很幽默很有魅力的结论。」
我们通过视频和庞博聊了聊,他会照顾你的感受,常常笑,时不时抛梗,「十分钟没出梗我就难受」,打断提问、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是举手喊「老师」。你能感受到他对于评价自我和袒露自我的生疏,但他依然在真诚地表达,他会感叹说评价自己好难,因为他总是想要客观,不想说得不对。他也会分析自己不习惯失败,不习惯负面评价,包裹自己、避免失败成了他安全感的来源。他对自己和职业有着很健康的认知——创作不会伤害创作,演出会拯救演出,这些认知反过来也让他走过五季《脱口秀大会》。
5分钟一场的赛制和网络愈发短平快的传播,让庞博的形象在一众新崛起的、具有锐利人设的脱口秀演员中显得有点平淡,但如果拉开距离,想想这几年,这个戏剧性发展的行业、飞速运转的赛制,把多少人抛下,就能多理解一分庞博「持续平稳」的可贵。
他仍然在思考脱口秀的可能。脱口秀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应该袒露自我、揭示缺陷、具有冒犯性、态度更鲜明?相对而言,庞博在话题和情绪上习惯性保留,他形容舞台上的庞博,是一个「不那么具体」的人,他不展示自己的冒犯性,也不习惯把自己置于被欺负的受害者形象,这些只是演员手里的道具,脱口秀不只是这些,对他来说,脱口秀不是关于自我缺陷的艺术,而是生活缺陷的艺术,但最终,好不好笑才是最高评价标准。
「我觉得有时候笑跟开心会分开,可能一个笑没有什么意义,就是笑,笑一个很奇怪的梗,笑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笑本身就挺好的,人们不是因为开心才笑,有时候人就是因为笑了,然后开心。」
这里面有一些纯粹的东西,就像他为自己选的离场音乐,《友谊地久天长》,演出结束了,好与坏都发生了,但只要我们彼此都认大家是好人,在做同一件事,友谊就会长存。
文|翟锦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记外)
往前走
这一季的表现,从前往后看我没有非常满意,从后往前看我是满意的,因为我知道大家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压力下在做节目,卷子做到这个份上我已经很满意了。
我的习惯是,要去参加《脱口秀大会》,以此为节点倒推我要做什么。春天准备,再往前面的冬天在休息,就像耕一块地,但是今年规划全都打乱了,春天大家都在上海,自己在家,做不了喜剧。又因为前面耽误了很多时间,后面整个工作行程是压缩的。《脱口秀大会》录7、8、9期的时候,中间只隔一个礼拜,大家创作都很不充分。到了半决赛跟总决赛间隔有两周,稍微充分一点。在这样的环境下,把应该完成的事情完成了,我觉得已经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了。
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掌控感的时候我会比较难受,但是在那个情况下还是能重新想办法,先掌控再失控再掌控再失控,永远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其实你还能往前走。
我今年比较明显感觉到大家希望别人成为他的嘴替,比较极端的是,如果你不是他的嘴替,他可能就完全不在意你在说什么。大数据也在做这个事,让更短平快的内容被大家喜欢。但我在想,脱口秀本身能装载的内容肯定是更多的,到底还能写点什么。
你总有你自己生活的偏重,但是大家未必能理解,他就当个趣事听。这一季的前两期,我们讲各自在上海的居家生活,他就觉得为什么都在说这个,他就觉得不好笑。不在上海,很难设身处地地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
今年的《脱口秀大会》,我最喜欢的是毛豆。他超级好笑,我很久没见过这么好玩的人了。我也不胖,我也没当过兵,我也不是厨师,但是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笑。他是非常轻快的表演,他没有负担,没有情绪,没有击中任何人的共鸣,没有做任何人的嘴替(笑)。我很少能那样轻快的好笑,我觉得这也太厉害了,怎么这么轻松就做到了。
这份工作的快乐浓度比一般工作高很多。创作出好的东西,你会先快乐一段时间,去看其他人的演出,也很快乐,生活中是没有这么多快乐的机会的。我觉得有时候笑跟开心会分开,有时候笑都没有什么意义,就是笑,笑一个很奇怪的梗,笑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笑本身就挺好的,我觉得人们不是因为开心才笑,有时候人就是因为笑了,然后开心。
节目录完,到现在我也没写啥段子,那会儿一个月要写四篇,后面需要一两个月才能缓过来,但是我能感觉到自己聊天出梗的能力在渐渐恢复。创作不会给人带来不可逆的损伤。你总归会有想写的东西,只要生活还在往前走,只要还在不停地感受周围,你就会有想写的。

庞博参加《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优等生
我没觉得自己是脱口秀优等生,因为脱口秀没有优等生。但是我能理解别人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我很多事就是会按好学生的习惯做,不出错,尽量做好,有规则就按照规则去执行,只要我认为这个规则没问题。
大家越来越觉得《脱口秀大会》像高考一样,一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脱口秀大会》,但它始终是形式很单一的表演,5分钟脱口秀,又要比赛,肯定会追求短平快,肯定要这5分钟非常好笑,但肯定有一些事是5分钟说不完的,有可能需要十分钟,这个模式下又不允许这个情况。
我觉得长远来说对脱口秀没那么好,但可能我天然就会考试,我不喜欢考不好,我肯定比很多朋友都适应这个规则。另一方面也是我锻炼的机会多,很多朋友第一年来的时候,不相信一个礼拜可以写出一篇稿子,但是这事你做到过一次之后你就相信了。我就是相信一天能写出一篇稿子,因为我已经做到过三四次了。我见过一个段子打磨了一年,「咣」一下就非常牛,谁都打不过;我也见过一个段子打磨了一年拿出来,没人理你。各种情况都有可能。你知道最好是怎么样,最坏是怎么样,无非就是在中间做调整。
其实很多事我没有特别想赢,但我特别不喜欢输。我特别不喜欢这事做得不好,自己或是别人给我负面评价。我挺怕犯错的,也没有足够的经验面对挫折,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那么直接袒露自己的原因,我需要一些安全感,就会更想躲开那些可能性。我那些考试,好像都是过了分数线没几分,但是你也过了,就是那种最经济实惠的过法。
我有些特质跟脱口秀其实是天然矛盾的。就像我打球不是特别喜欢投篮,喜欢除了投篮之外任何能让球队获胜的动作,听相声也是喜欢捧哏的超过逗梗的。我始终不会冲得太靠前,会在话题和情绪上有一些保留。我们举邱瑞海底捞的例子吧,我写这种段子就会想,我如果在台上吐槽是不是不太好,因为我在吐槽一个具体的人,他可能会受到伤害。我也很少在段子里吐槽我爸妈或者是我太太,因为那是一个更具体的人,你吐槽TA,你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TA是OK的,所以我就会往后退一步。
我在台上不太习惯让自己是一个倒霉的角色,比如我吐槽父母催我结婚,我在段子里是受害者,但是我不习惯自己在舞台上是这个形象。我生活中很少处于被欺负的状态,我会尽量避免。像志胜,他刚开始写外貌,他其实就是在被欺负嘛。但客观上我没被欺负,我也不能欺骗观众说我被欺负了。在我的感受里,缺陷是你的第一个5分钟,讲完了,你不会一直谈论这件事情。
脱口秀做的时间越长,你写的东西越来越多,终究还是对当下生活的观察,以及这个观察跟你自己产生的联系。我不觉得脱口秀是一个关于自身缺陷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总归是会有很多缺陷的。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也不是发生在你身上,是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生活里不太合理的事,基本上都是有人在「欺负」我们。大家为什么上班要花钱排队去买一杯没有人爱喝的冰美式?工作本身就很繁忙了,为什么还要非常疲惫地挤一小时的地铁上班?地铁都这么挤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来上海?大家为什么会不得不来上海?
比如看到卫生巾广告,我也觉得很不合理,我就觉得「被欺负」了,但是那个「被欺负」的人确实不是我。我讲卫生巾的广告为什么都是年轻的女明星代言?好像有一个隐形的门槛一样,为什么没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师来代言?她们不是经验更丰富吗?我也写了很多这种段子,也挺好笑的,但是我不会以「被欺负」的角色来写。
对于「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这个观点,我持反对意见很久了。毛豆冒犯谁了?多好笑啊。我不觉得他冒犯到任何人。
我其实性格里是很有冒犯性的,只是我不在脱口秀里把它展示出来,我没那么想展示这些东西,有时候是还没有用玩笑的方式把它处理得非常好。好笑是最重要的,效果好是最重要的,今天的演出成功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脱口秀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演出,里面的表达、冒犯、态度、观点、身份、人物设定,都是演出的因素,是我们手里的道具。在很多观众看来,这里面的一些东西是超过演出本身的,但这是脱口秀啊,又不是演讲。
把荒谬呈现给大家,这是我创作上的出发点。但脱口秀对我来说最珍贵的就是你能逗别人笑,你能获得满足感跟成就感。你讲了一个段子观众会由衷地开心,你知道那是对你又一次的认可。

庞博在线下讲脱口秀 图源庞博微博
意外
我人生最大的意外就是讲脱口秀。真的,非常意外。你没有任何目的地去看了一个演出,去演了开放麦,然后就到了现在。
在这之前我的人生都是按部就班的。从小成绩很好,受老师家长的喜欢,目标感一直很强,一切都是为了高考。成长过程中没有什么意外。我没逃过学,也没有跟谁去哪儿玩的回忆。小学的时候,我跟几个同学一块回家,同学说咱们去哪儿玩会儿吧,我就跟着去了,但发现外边也没什么好玩的,我就趴在墙头上把作业写了,回到家还倍儿自豪,作业写完了。但爸妈因为找不着我,很生气,我妈还哭了,后面放学,我就都准点回家。
我也没叛逆过。就是好好学习,不给家里添乱。如果说有遗憾的地方,就是我大部分的记忆都跟学习、考试有关,我没有意外。
生活一直按照规则,按照某种习惯的约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有很明确的目标感,上学时拿到好成绩,毕业后要找一份好工作,工作后想在上海买房,像打游戏一样设定目标。但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了。游戏里突然没有了Boss,也没有结束,很奇怪地,你就站在原地。
刚开始我也会拿公司的体系框自己,但很多时候框不进去。上学的时候你对未来充满未知,充满可能性,但工作之后,你发现可能性一下就变得很小,你从事了工作中的一种,你工作里的上升、改变也很小。
工作之后,我觉得人是很渺小的。上学的时候,我的自我是比较强的,虽然一直按照规则做,但是我在学习知识,我在这个体系里证明自己。工作之后,自我一下子就变得很小,你变成组里的一员,可能两三个月都在写同一个Feature,实现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在整个产品里只是一小块,产品丢到市场里,又是很小的一个东西。
你也会看到很多同事,我三年之后是不是对角线那个人的样子,五年之后是不是老板的样子,十年之后是不是我老板的老板的样子。我觉得他们也没有那么有趣,无非就是手下有一个Team,手里有几个项目,每天在邮件里跟各种老外撕扯。虽然他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也没那么羡慕他。大家中午吃饭聊天,是不是应该买房子了,小朋友要上学了,小区地面因为地下水出现沉降了……我就觉得人一下子变得很小很具体,有点难受。
幸运的是,我碰见了脱口秀,如果没有我可能也就继续工作下去,我可能做得没有特别好,也不会很差,就这样继续下去。

图源笑果工厂微博
2016年9月,我开始讲第一场脱口秀。笑果在徐汇有个开放麦,我去看了。我当时是现在最讨厌的那种观众,因为接下茬。我现在还是认为接下茬是不对的,但当时确实是那个演员讲错了(笑),完了觉得自己还挺幽默,就去讲了。
开放麦在酒吧的二楼,平时是仓库,他们归置出一块地,放一个舞台打上光,也就十来个观众。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讲了啥,当时也不懂什么叫段子,只记得舞台的光特别亮,根本睁不开眼。因为没演过,一上去就紧张,把准备的东西背完,也不咋好笑,但那会儿也顾不上好不好笑,匆匆忙忙就结束了。
你还记得《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我最后讲的那个段子,我来自河北,河北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省份,但这个事媒体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提到河北永远都是北京、天津及其周边区域——那是我写的第一个好笑的段子,是我第二次开放麦写出来的。开放麦就是那样,你有好笑的段子你就能瞬间证明自己。挺奇妙的,像《桃花源记》,初极狭……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笑声跟掌声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认可,你「咚」一个梗,大家哈哈一笑,你非常有成就感。
说了不到一年,我就去录《今晚80后脱口秀》,后来就是《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录完《吐槽大会》第二季,我跟李诞聊了聊,他说来试一试呗,不行你再回去写程序。当时我也工作了四五年,碰到第一个槛。大家一开始都是很初级的员工,总会有人先升上去,先变成小组长,我不是走得最快的那个人,职业上有一些瓶颈,那就不如试一试。本质上我还是比较关注自己的感受,很容易就做了选择。
来笑果全职讲脱口秀,战略上非常冲动,但战术上非常仔细。我跟他们仔细谈了谈应该给我多少工资,应不应该给我交公积金。他们也问我当时挣多少钱,我也很诚实,我说我挣多少钱,他说要不就差不多,我说是不是有点少啊?他说那再涨两千吧,我说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始终觉得我很幸运,我讲脱口秀以来,脱口秀就不是一个需要你赔钱创业的工作。我也没经历很多艰辛,好事都赶上了,《吐槽大会》一下就被大家看到。跟其他人比起来,最开始笑果没人投钱的时候,老叶自己拿积蓄投,程璐、思文、海源他们都是从深圳搬到上海来,都比我的转变大。我更多是一种自我实现上的思考,不涉及生计。我就是很顺,很顺利,也很流畅。

没那么具体
最开始讲脱口秀,讲什么是很明确的,因为观众还不认识你,你就讲你是谁,从哪里来,过往那么多年的人生里,总归会有些好玩的事情。但是后来,你吐槽了父母,吐槽了结婚,也吐槽了职业,自己的那些东西差不多快讲完了,到《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第三季,我创作上陷入困难,反复困于要跟大家说什么。
第二季那会儿我一直在想,如何能在台上展现更直接、更赤裸的自我,但展现出来的,是比较焦虑的一面。我当时觉得,你往自己深处走得更多,会更打动人,那我要在台上毫无保留,像一个精神暴露狂一样,把所有东西都袒露给大家。就像Bill Burr,他在台上会说一些偏颇甚至歧视的观点,你有时候会想他是不是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能在笑话里完成自己逻辑的自洽,我当时觉得这个还挺厉害的,这样也会很好笑。
那几年我咣咣拿自我出来,但发现真心只会换来真心,不会换来票数(笑)。比如决赛的主题是「笑是生活的解药」,我讲的是微博上的朋友发私信说他的家人因为意外需要卧床,看《脱口秀大会》很开心,但是无论这事你多想说,写得不好笑,就会很难受。还是要好笑,好笑了就一切都通,都顺。
我后来发现脱口秀有很多种,很多人完全不讲这些,就讲生活中地铁很挤,装修很吵,只是种类不同,但都是好的脱口秀。我那会儿还问过李诞我该说什么,他说你就写你周围的生活呗,写你的父母,写最亲近的人,写那些不会觉得被冒犯、被伤害的人,我虽然最后也没完全这么实施,但是有一些思路上的启发。
缓解你对问题焦虑的方法,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本身。第三季结束之后,我的创作才有了转折点。那是2020年底,我写了一个专场,起了个名字叫「三件小事」, 讲了三个长长的段子,一个是网络暴力,一个讲卫生巾,一个是王思聪来看演出,一件事讲个15、20分钟,我发现这些小破事也能讲很久,也挺好玩,挺适合我,原来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写。而且我发现,虽然我在节目上表现没有那么好,但是回到剧场,大家还是给你比你想象中更好的反馈,不会以节目上的名次来直接肯定或否定你这个人,你能感受到这个事还是能继续往前走。
脱口秀演员都会把自我拿出来,但是肯定是拿好笑的那一部分,比如愤怒可以处理成好笑的情绪,内向可以处理成一个好笑的人格,但是我的人格里有很多拿出来也没那么好笑。比如我原来想写我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发现写不出来,没什么细节可以填充进去。到现在,我也没有不把自己袒露给观众。大家知道鸟鸟是一个那样的人,呼兰是一个那样的人,庞博是一个那样的人,我的那个就是没那么具体,但是你也能感觉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可能就是一个没那么具体的人,但我也不向往比如像邱瑞,或者是鸟鸟。提到邱瑞,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愤怒、什么事情都很看不惯,但是又弱弱小小的人(笑)。我很欣赏他的表演风格,但我也没有那么想成为这样一个人,我也不想让大家一提到我,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印象。
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也许我就是没那么具体,人是变化的、流动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不愿意向我不熟悉的人袒露过多。因为我怕我的评价是不对的,这是下意识的,我就不希望这个东西不对。
你得理解,Bill Burr在扮演「Bill Burr」,在台上我是庞博扮演「庞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你可以这么认知我。如果认为你在台上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有点吓人。

庞博讲开放麦 图源庞博微博
目标感
原来我做脱口秀目标感很强,你要录《脱口秀大会》,你要参加《吐槽大会》,你要开专场,你可以照着一个已经成功的范本这么做。但是现在接下来要做啥呢?我其实有点想不明白。
很多朋友都会来问,你下一季参不参加?我的回答是你先得保证有下一季《脱口秀大会》,也要看下一季《脱口秀大会》长成什么样子。下一步要干什么,这是一件很难想明白但是一直在想的事情。
我有过情绪很差,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可能一个段子都写不出来的时候,但没有退出行业或不参加《脱口秀大会》的念头。因为在过往的时间里,除了《脱口秀大会》,也没什么别的舞台。虽然有些时候真的写不出来,但我仍然觉得脱口秀有意思。写出一个段子仍然是很开心的,你把这个段子讲给大家,大家笑了、鼓掌了,仍然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始终没有丧失过热情。
我也会想接下来是不是要做更多的事情。尤其今年,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出去录一些节目,跟大家聊天时他们会说,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你,但是又没有那么了解你。很多人都看过我们的一些片断甚至看过节目,但除了这些,大家没有太多了解我们的机会,我可能会多尝试一些,最近录的真人秀节目,大家没有什么包袱、梗,就是在规则设定下做一些游戏,观众也真的很开心。我发现,如果说成就感来自看到观众开心我们就很开心,奔着这个目的也不是只有脱口秀一条路可以走。
我现在就觉得,要接着好好写段子。
现在我在脱口秀上已经没有很具体的目标了。我写过专场,也去演出,只是现在这个环境很难巡演。我也不会以《脱口秀大会》拿到什么成绩来作为目标驱动我,它最后就是决赛那一场演出决定的,这是一件非常随机的事情。你没办法把自己托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目标上,它对你也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人为什么要有目标?就是为了说服自己要继续做这件事。在我看来,写段子就像跑步一样,我也不是为了跑马拉松而练跑步,我就是跑。我现在不再需要一个具体的目标,我就是要跑起来。
《友谊地久天长》,这是这季我选择的离场音乐,也是我专场的离场音乐,挺好听的。做完一场演出、一场节目、一场秀,结果好与坏,都已经发生了。有时候我好笑,有时候我不好笑,一年做下来有苦、有累、有容易、有不容易,有人意气风发、有人特别憋屈,但是这么长时间跟观众处下来,彼此都是个好人,是一起做事的,大家还是认的,那大家继续处,就希望这个事长久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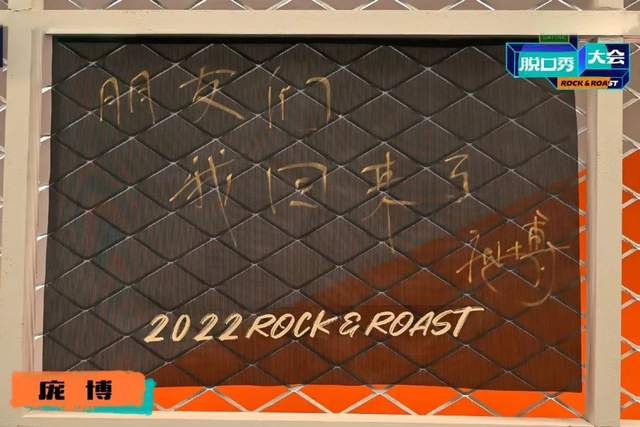
《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开始时,庞博写的「冠军旗」——「朋友们,我回来了。」图源脱口秀大会官微
TOP STORIES
相 关 推 荐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