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片导演傅东育如何拍一部主旋律?

画面里,一个300多斤的大男孩被一位女性柔道运动员反复抱摔、背摔,身体不断地向地面砸去,发出巨响。他是国家女子柔道队的陪练刘磊磊,在过去16年里,他被摔了284万次。刘磊磊的名字曾经在一些简短的报道中出现过,又很快沉了下去。
但在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中,刘磊磊成了其中一集的主角,那一集,取名《磊磊的勋章》。
《理想照耀中国》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题重点作品,与很多拥有宏大命题的电视剧不同,它将镜头对准了40组普通人——16个分集导演,40组人物故事,76天拍摄完成,总导演傅东育最终带领团队完成了这项不太可能的任务。
作为一位拥有28年从业经历的资深影视剧导演,傅东育曾经执导过《医者仁心》、《国民英雄》等电视剧,前后获得了两次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那是个公共讨论远不如现在蓬勃的年代,他拍摄的电视剧的声名远比他本人更为响亮。
他最近播出的一部作品,是电视剧《破冰行动》。这部警匪、缉毒题材的电视剧在2019年5月开播,斩获的成绩相当耀眼,在网络走红后,它又获得了第26届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傅东育的名字被晾晒在太阳之下,行业和更大的圈层才渐渐发现他。
面对《理想照耀中国》,傅东育要做的,是在面对这个理想时,去实践自己对于整个影视剧行业的理想——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出身的傅东育坚信,影视剧创作是一个有着严格标准的工业流程,它需要用绝对达标的技术,去完成最终的情感碰触。
傅东育如今53岁,语速飞快,恨不得将过去30年的感受全部掏出来,讲给采访者听——1993年拍摄处女作至今,他经历了中国影视行业从蓬勃起飞到曾经失准的过程,如今泡沫散去,他依然还在这艘船上。
在《人物》与傅东育的交谈中,他多次表达了对影视剧工业化标准诞生的期待,作为一位入行超过30年的导演,他也一直在呼唤影视剧工业化专业标准的回归。这一次,他讲述的,是一个怀揣专业主义理想的导演,如何完成理想这个命题的故事。
以下是傅东育的自述——
文|林念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化妆|钗钗
守护华丽羽毛
出任《理想照耀中国》的总导演,最初我是拒绝的。
去年9月份,我还在拍电视剧《冰雨火》,总制片人王柯就来跟我聊。他说,有这么一个项目,叫《理想照耀中国》,时间很紧,第二年5月份要开播。他说,你来当这个总导演。我说,这事我不行。
我写了三封请辞信,都被拒了。但我还是想躲。
和很多主旋律剧不同,《理想照耀中国》写的不是英雄和伟人,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尽管我一直说NO,但在不断的审视和讨论过程中,我对那些人物也代入了自己的情感。作为一个导演,我也会被感动,也会想拍他们。经过思考之后,我觉得至少可以一试,成不成不敢说。
既然不跑了,咱就准备干吧。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幸福感,包括开机那天心情都很沉重——我害怕完不成。
2020年12月28日那一天,在上海,东方卫视有一台晚会,是总局向党华诞献礼重点影视剧展播启动仪式,主题就是理想照耀中国。《中流击水》《大决战》《百炼成钢》《功勋》《光荣与梦想》……所有导演、主创全在后台,一水儿地站好,20多个人。全场只有一个导演脸是笑不出来的,就是我。我当时剧本还没有,分集导演都还没搭齐。那个时候,有些剧都已经拍摄完毕了。所有人在后台看到我,都是一言难尽的眼神,你这有点难。
焦虑,做梦都是这些事,那就别睡了,睡两三个小时肯定醒。做了20多年的导演,没有任何一次紧张到那种状态。责任、压力太大了。《理想照耀中国》,天啊,你要拍砸了怎么办?我每天晚上跟我太太打电话,你老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煮熟的鸭子,只有嘴还在动。
首先,要挑导演。我见了80多个导演,多的要聊上3个小时左右。挑选的原则之一就是他们必须接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尤其是接受过系统的导演训练。他们有在法国、英国读的,有在美国读的,北电的、中戏的都有。比如,郑世龙导演,他是1987年的,在法国念过书,他拍的有一集叫《纽扣》,讲的是19岁的少女章华妹,从在街边卖纽扣到成为中国首个个体工商户的故事,郑世龙就把80年代的中国乡镇拍得非常的浪漫,非常新浪潮。
还有一点,我会尽可能地去选择有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人,他们必须有实操的经验,按照现实主义的路子走过的,而不是拍一些悬浮的作品。这些要求,构成了这样一个导演团队。他们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在35岁,在这之前都没有太高的作品,都是很扎实地在剧组工作,在培养着自己。
我当时写辞职报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戏拍不成,它会让我前几十年艰难地争来的华丽羽毛,瞬间被拔掉,说你看这个导演拍的什么玩意。如果它失败了,没有人问我,你花了多少时间、给你多少周期。
但这个剧组的团队是我这么多年来当导演没有见过的。去年12月那个时刻,剧本还没出来,一集最多只能拍十几天,没有几个导演会接。但他们接了,没有那么多顾忌、游移、患得患失。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初心,是对这个行业的热情、欲望、表达。

总导演傅东育在《望星空》单元拍摄现场
真实
接下来,怎么拍?一个一集25分钟的剧,一开始大家基本上都没概念,能做什么,口述历史还是栏目剧?
何为理想、如何照耀、照耀在哪里,这个剧的六个字,得说清楚。《理想照耀中国》的定位是诗选剧,并不是说它的表现形态是诗歌一样,有些篇章是拍得非常浪漫,非常诗化,但是诗选剧这个概念,是极度的凝练和高度的升华,在这一方面它确实像一首诗歌。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类型化和个人风格越清楚越好。统一的只有一个,我跟他们说,每个故事回到我这里,我要看到温暖。
要温暖,前提是你能摸到他内心最柔软、真实的那个点。我跟所有的导演都说,好好说故事,章华妹不是那个女老板,是她想活得更好,努力卖掉这颗纽扣的样子。这就是她的理想和人生希望,这就够了。
所有导演要跟原型人物聊天,只要他还活着。如果原型人物牺牲了、去世了,那就要跟最熟悉他的后辈们聊,走到那个地方去,看他的史料。虽然有的在横店搭景,但是要去歌乐山,要去看渣滓洞。时间来不及了,导演就和编剧一起出发。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间再紧,也得按照这个来。跟原型人物聊天的过程中,他打动你的那一刻,破题点可能就在那了。
每集只有25分钟,其实还可以压缩到15分钟。一个故事的真与假跟时间长短没关系,而是要还原真实的年代。那个年代梳什么样的头、戴什么样的耳环、说什么样的话、用什么的遣词造句,演员的表演是否符合那个年代,这都是要做到的把持。所有的细节要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
为了真实,导演们都挺执拗的。《雪国的篝火》的故事原型是红三军团第六师十七团一连炊事班,这个炊事班有9个人,在长征翻雪山的过程中全部牺牲,但他们让整个连队都得以保全。导演刘国彤坚持要去原地拍摄。我不同意,我说,5000米海拔,你设备都抬不上去。我们打了3个小时电话。我说,你去长白山吧,长白山的海拔不用那么高,但也有3000多米的海拔。剧组100多个人。就在雪地里面扎了9天。

《理想照耀中国》之《雪国的篝火》剧照
还有演员。王劲松选的就是《雪国的篝火》。我跟他说,你想清楚,他说,我想清楚了,你还能找到中国比我更瘦的,适合这个角色的呢?我说有啊,他说谁?我说,我啊。为了这个剧,王劲松在10天内减重了20斤。因为要贴近角色,平常的生活习惯就要跟那个人相近,老钱就得饿着。
《理想照耀中国》播《叛逆者》的那天晚上,当陈晓最后喊出共产党万岁,我看到评论里,很多人说瞬间泪奔。这就是因为表演、镜头的赤诚,导演的赤诚。那个镜头是导演在现场先示范,接着让演员瞬间代入的。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原则,我们相不相信这个故事,我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有没有基本的情感。
我还记得,开机的那一天,大部分导演都在横店。我说,所有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还是有情怀的。你是对这个国家和对这个党,不管你是不是党员,你是自豪的,你是热爱的,否则拍不好。
其实当时接这个戏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问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在党的百年,你真的不想做点什么吗?下一个党的百年,我应该已经到天上去了,不在现在这个时刻留下一点什么吗?黄建新导演今年拍了《1921》,刘江导演拍了《光荣与梦想》,无论如何,大家对于党的历史,在这一时刻交出了应该交出的作品。

工业化与手艺
其实,《理想照耀中国》很像我读大学之后交学生作业,它很像一个学生作业的体量,但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它的工业化程度要求会更高,指标也更高。
工业化是什么?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学的导演,在我的大学经历中,我接受的理论是,你首先要在工业范畴体系内谈你的作品。在一个工业体系流程范围里,你的定位是什么?我想谈技术,我想谈工艺。
《红高粱》上映那年,先去北影放映,后来又去上戏放,张艺谋跟导演系的学生一起座谈。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张导演我想问,我们提的问题跟北京电影学院提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你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告诉你,北京电影学院就是——你那是什么意思?你想解读的是什么?你们这儿问我——那个太阳怎么拍的?你租了多少地?
上海的老师永远告诉你说,来,你先把正反打给我拍清楚。你先搞清楚为什么剪片子之后,说这个镜头我要过肩。这是手艺,正反打都没有讲明白,你跟我说长镜头,你跟我说移动,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工业流程。我们1990年进入上影厂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电影制作手册,蓝皮横开本,每个工种的要求按照美国来。美国到今天还是这样,每一个员工都穿着翻毛皮的皮鞋,戴着胶皮的手套,所有电线一捆一捆缠得非常好,一排排堆在墙角,一个镜头拍完收拾好,到下一个镜头再拿出来,不允许漏电。
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现场,线绕线、线滚线。掌机的那些小摄影,上一部戏还在跟焦呢,跟焦的上部戏还在推轨道呢。但是在欧美和日本,一个推轨道的能推10年,只干这个。这很像上海电影技工学校那时候,招初中毕业生当技术工人。工人们知道轨道是什么样,点点滴滴的细节构成每一个镜头。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机制了。我们曾经拥有过的体系已经完全被打破,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再建立。我们在呼唤影视业的蓝翔技校技术工人,但还没有出现。
这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做到的。我在现场,无非就是着急,这个还要教吗?这个还要说吗?这个轨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演员情绪非常好,结果焦点跟丢了,你恨不恨?
工业文明时代以后,才有了影视这个艺术形态。当有了照相机开始,有了摄影机开始,我们开始有电影,从16格的到24格,从无声变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到现在3D。从它起始这一刻开始,它就是工业化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一直到制片,它一定是一个集约完成的事情,和建一个工厂是一样的。谁能把这几个维度都做到最好,这个作品肯定好。
所以,拍《理想照耀中国》之前,我在跟各位导演在聊时候,就要求了,25分钟体量范围之内的起承转合,要精准到每一句台词,删减掉每一个不必要的场景,要浓缩到不需要废话,必须要有留白,让观众在看的过程当中产生跳跃,自己填补一个空间,而不是娓娓道来,这和长剧拍摄是很不一样的。

总导演傅东育拍摄现场工作照
网感与性感
我今年53岁了。在我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是非常幸运的,赶上了从1978年开始的十年思想开放,各种理论、学说一下子都涌进来了。
我在上戏上学的时候,院长是余秋雨。余秋雨说,上戏是不熄灯的。我们培养的是学艺术的孩子,他们将来是艺术家,他们怎么可能半夜熄灯,他们这个时候可能都在创作呢,或者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在大学里接受的文化教育,和对人文素质的培养,我们对哲学概念、人生的探究至少不那么市侩和功利性。我赶上了那个时代。
离开学校后,我被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从道具、服装,还有洗印干起。后来自己写了个剧本,1993年,拍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身不由己》。1994年以后,我开始做电视剧。
从那时一直走到今天,我几乎没有一部电视剧赔钱。这点就是活着的本事,剧本再烂,我都能给出标准质量。这个剧,只要我接了,我总能找到那个让观众买账的切口。2008年,我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医者仁心》,让我第一次拿了飞天一等奖。拿奖的第二年,《国民英雄》又让我拿了一个飞天一等奖。

《医者仁心》剧照
这些年,我拍过古装,我拍过喜剧,我拍过青春片,我拍过惊悚戏,我拍过律师剧,我拍过医疗剧,没有一个类型是一样的。导演在我脑子里面,渐渐变得不再有那么大的光环了,它是我的手艺,我是个手艺人。
很多人认识我是在电视剧《破冰行动》。它是我拍的第一部网剧,实际上在《破冰行动》之前,我是打算退休的。
准确地说,尤其是2015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影视的评价体系在崩塌,变得混乱,人人都可以当导演。我骨子里是悲观主义者,我并不认为这个行业处在特别好的状态。网络鱼龙混杂,这个混乱让我无所适从。
在这种浮躁的环境下,我和片方谈崩的时候太多了。《破冰行动》制片方第一次跟我面对面的时候,说导演,我们要网感,我说,网感真不懂,性感我懂。
我以前那套老手艺不用改变,但还是要学习。当年拍《医者仁心》之前,我把医疗题材的好剧几乎都看了一遍,然后设定一个标准。拍《破冰行动》之前也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去看大量的优秀剧集、去学习。国外的一些警匪戏,对体制的思考,或者对于人性的思考是更深入的。将人放到一个极致的戏剧状态之下,迸发出人的力量,人性的挣扎和拧巴就会浮现。
从一开始拍,我就没认为《破冰行动》仅仅是一个涉毒罪案剧,我想讲宿命的问题,你的命运自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已经定下了,只是你想改变它吗,怎么让自己脱层皮。这是宿命感。它是有信仰的力量的。最后,它能够破圈,成为爆款也是因为这个。
从类型片的角度来看,《破冰行动》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但它的遗憾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做得更加类型化。
工业化流程的第一步就是类型化,把片子归类归清楚。我跟你说实话,90%,我们的作品拿出来,归类归不清楚。现在要看律政戏,有多少律师在那儿谈恋爱。
《破冰行动》是警匪剧,这个类型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比例要更加精准。一个类型片警匪戏里面,动作戏应该占到多少?25%到30%。如果低于这个数字肯定不过瘾,但也不能超过1/3,不然就成了动作片。
还有,警匪戏里的情感到底应该是多大分寸?爱情线必须得有,但它必须要高级。爱情必须进入主要侦破的事件本身,男女主角裹挟进事件里,如果不是,那撒糖是撒面上的,是撒不明白的,它破坏了这部类型片,这也是《破冰行动》让我反省的一件事。
作为导演,需要做的另一件事是——不管演员是年轻还是年老,把他们的能力拉在一个水平线上。包括电视剧《冰雨火》开机时我就说,绝不允许年轻演员在这部戏里面只负责颜值和流量,而年长的演员负责质量。
在技术层面的基础上,工业化的第三层标准就是情感的触碰,以及,主题还要有升华——观众在感动之余,影视剧对他的人生有没有引领。
这些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功课做得再深入一点点,自我检讨一点点,关键是你做不做这个功课,愿不愿意去分析这个事情。
尽管《破冰行动》有很多遗憾,但拍完以后,我发现,千辛万苦坚守到现在的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还是被认可的,我对工业化的要求、对类型片的理解是对的,是有市场的。我赢得了很多同行的信任,我就要更加珍惜这个信任,你没输,标准还是这样的——这个市场,也突然让我觉得我有价值了。

《破冰行动》剧照
现实主义与主旋律
现在,别人如果说我是一个类型片导演,我觉得会是无比荣光的褒奖。我没有理由跟所有人说,你看看吧,我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我有什么资格?我总觉得那个很虚妄。导演这个行业,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工作,是当你终要离去的时候,看所有的作品,它们会在一个水准线上。在某一个类型做得非常有成就,或者有口碑,当一个匠人已经很棒了。
回到《理想照耀中国》,我的手艺、技术,就是让大家对这样的正能量、充满主流价值观的作品,开始有全新的理解了,尤其是年轻人,大家的口味在变化,开始接受这样的作品了。曾经有十几年,我们玩的不是这个,是穿越,是无脑,是甜宠,像那种工业糖精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当大家浮华洗尽,走到今天,所谓的回归就是,孩子们真正感动的是什么。没有思想内涵,悬浮感更强,就是年轻人爱接受的吗?面对年轻观众,其实方法是没有变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情动人,拍的是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啊。

《理想照耀中国》之《第五十五封信》剧照
其实,在此前的一些创作中,我们把主旋律概念化了,甚至妖魔化了,把主旋律高高地放到了一个天花板的位置。对我来说,我理解的主旋律是表达这个民族、这群人、14亿人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对生活美好的愿望,以及我们的理想,当你开始表达这个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主旋律。于是,你的所有生活细节的枝微末节,包括对于历史、对于今天的印照,都会在作品中有着润物细无声一样的表达。
事实也证明,主旋律在过去这一年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我们应该深入去研究现有的优秀主旋律作品到底为什么打动观众?
比如快递小哥最后拿了中国诗词大赛冠军的故事,这个选题一开始是被我拿掉的,我说这个没法拍,但韩可一导演对我说,你不觉得这个诗歌的美是一种传承吗?当下生活中所有的艰难,可以通过诗歌的美来疗伤。我瞬间被他打动了。我说你准备用什么手法,怎么架构你的故事呢?他提出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拍。韩可一最后找了快递小哥真人拍的,他让他跟李白在对话,跟李白吟诗,多有趣啊。
《理想照耀中国》每天播一集,播两个月,大家每天花半个小时的时间,静静地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笑或感动,想了解他们,我觉得美感应该是这样产生的。
《理想照耀中国》有一集,叫《一家人》,讲排雷战士杜富国和抗疫者杜富佳兄妹的故事。播出以后,他们传给我一张照片。照片里,杜富国在听我们的电视剧。他在一次扫雷排爆的时候,为了保护战友失去了双眼和双手。那张照片中,一个ipad搁在桌上,他就在听。他的妹妹杜富佳给演员李一桐发了微信,表达感谢。还有一天晚上,《叛逆者》那一集的原型何敬平的亲生侄女,写信给编剧,说能不能送我一套碟,我要珍藏。多么动人,这就是这部剧的意义。
《第五十五封信》里的陈毅安将军的孙子,是个火箭军的少将。那一集播出后,他写了一封长信,代表他的爷爷和家人,说感谢你们把中华民族的美和守护传承了下来。《磊磊的勋章》播完了之后,整个的青岛柔道队多么开心,我们有价值了,陪练很伟大。

《理想照耀中国》之《磊磊的勋章》剧照
拍《理想照耀中国》,有一个场景我记得很深。其中一集叫《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讲述了在西藏玉麦的一家人,守护祖国国土的故事。那一集的拍摄地就在西藏玉麦乡。它是中国最大的乡,3000平方公里,麦克马洪线穿越当中。这是我们的领土,紧邻着印度。
2月初,我前往玉麦。路很不好走,得从横店坐飞机到拉萨,接下来还要开车走14小时,横穿喜马拉雅山,抵达南坡。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吹到这里,那个地方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西藏,是一片雨林。
我之前问过分集导演,你为什么非要选到这里取景?但是当车开过去的时候,我一看,突然就明白了。一片山坡上有八个大字,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一根中国国旗立在那里,一家三口人在那里守了33年。到今天为止,这个乡从3个人变成40多户人家、247口人,还通了路。
条件依旧很艰难。5100米的海拔,没有梯子,剧组拍摄的时候只有一根绳子,每个人跟蚂蚱似的,把拍摄设备一个一个通过手传递下去,然后是递暖瓶、递方便面。
所有剧组人员分住在老乡的家里,我们和藏民的生活习俗完全不一样,没有吃的,满屋子都是方便面,蔬菜很昂贵。唯一一家汉餐饭馆,是一对四川夫妻开的。那天我跟总制片人王柯说,今天晚上小年夜,请大家吃顿饭,吃吃饺子吧。那个汉餐馆摆两张圆桌,老板又把卧室床拆了,又架了两张桌子,贴着灶台,所有人就得这么挤着。我们站起来敬酒,一桌桌敬过去。那一天,王柯是哽咽的,我是哽咽的。
我们在拍着理想,同时被理想照耀着。现实主义是在血脉中的。
在今年所有的建党100周年主题片中,《理想照耀中国》可能是奇葩异朵,它不宏大,它只是一朵小浪花,但是,这朵浪花却有着很大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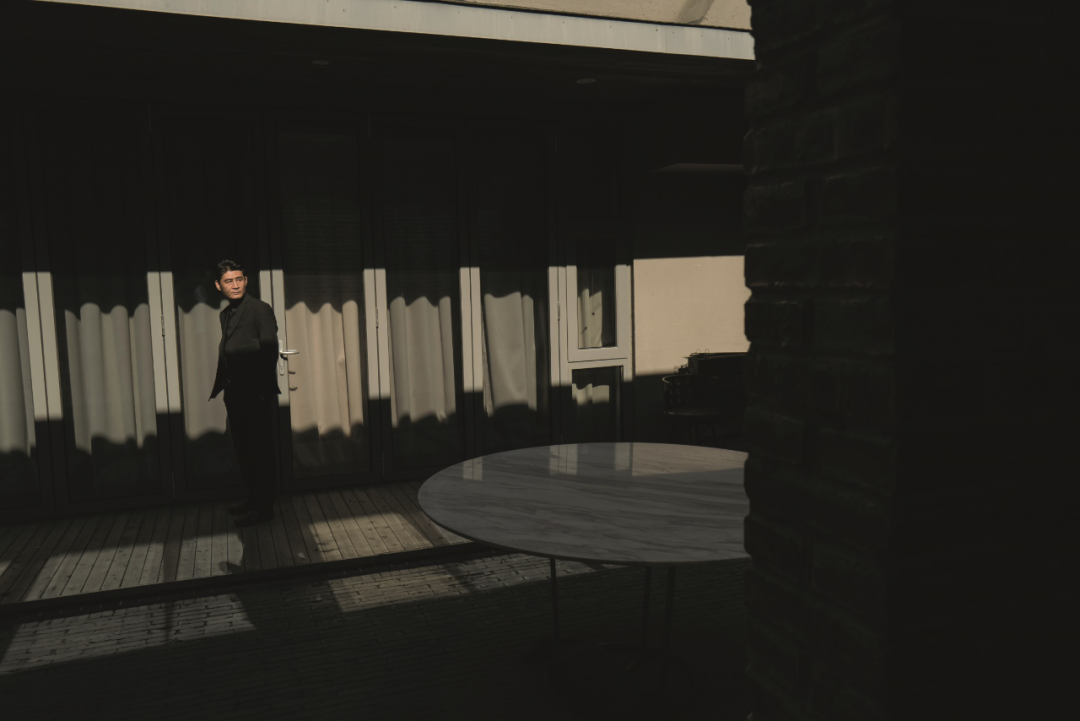
TOP STORIES
相 关 推 荐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