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丘旁
我不知道他们疯了还是我太正常,和热衷研究外星人的朋友在一起我不思考外星人的存在是不现实的,我感觉我们正在打破某些界线,期待着天外来客的光临。

以下为《人物》小说课优秀作业系列的第八篇小说选登:
文|石沉
1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门,东门和西门。西门比较大,宽阔,学校的宿舍就在西门边,稍有资历的老师都在那分到了宿舍。我的同桌小路就住这里,她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也因此周末不得不去各个老师家补课。我通常走东门,五六分钟就能走进院门,我常对着门口站岗的兵哥哥敬礼,他们的岗亭上写着「士兵严肃,不容侵犯」,他们并不会向我回礼,但是会偷偷冲我挤挤眼。我住在海军部队家属院,听起来很光荣,但其实是个秘密。部队的地址不能随便泄露,每天晚上在院子里遛弯长达一小时的前司令有一次神神秘秘地跟正在玩地道战游戏的小孩们说。我们都很信服,毕竟常常出海的父亲们就像院子的游客,十天半月回来游览一番,看看各自的孩子是不是缺胳膊少了腿便又离开了,曾经的司令在我们眼中是最大的人物。从学校东门出来的,还有旁边南山岭的学生。南山岭是个外来人口聚集的村子,摇摇欲坠地驻扎在这座小城的边缘地带,居民都是东三省地区南下务工的人,多数拖家带口而来,他们的孩子也就借读于城市最西端的我们这所小学。南山岭的学生们没有一个好惹的,夏天个个都汗津津、臭烘烘,眼神里多少带点凶狠。
王权是南山岭众兄弟姐妹里的大哥,个子不高但是够壮,据说是从小帮家里劈柴练出来的,我们冬天烧暖气,没有他的体魄也是无可奈何。王权上了两年四年级了,脑袋里除了打架和炸鸡皮没别的,冬天就算挂着鼻涕也能随时挥舞着拳头吓得五年级的男生掏钱给他买20串炸鸡皮。虽然我和王权来自不同的大院,但是坐前后桌产生了深厚的同窗之谊。我虽然也觉得他脑子有点笨,但是他打架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孤勇,我相信他的世界里一定有某些我不知道的秘密。我们常一起找老祁买刨冰。同住南山岭,王权对老祁倒是毕恭毕敬。忘了从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开始,老祁就在学校东门口卖刨冰。他的刨冰不是夜市那种现做的,据他说是因为学校门口的土路灰尘太大不干净,他每天做好足够的 刨冰,放在他的保温桶里骑车驮过来,融化了些许的刨冰没有锐利坚硬的冰碴子,口感绵密沁人心脾,起初我都不敢相信老祁这样看上去木讷,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中年男人竟能做出这样的美味。老祁的冰桶放在今天来看可以说是高级灰色的,放在他那辆虽旧但是一尘不染的三轮车上显得亮堂堂的。桶的内壁则是奶油白色的,里面通常盛放着满满当当一大桶粉红色的刨冰,春天大块的草莓颗粒分明看得清果肉纤维分布的纹理,盛夏的时候切得工整方正的西瓜渗出汁水和刨冰的颜色暧昧不清。通常放学的时候天气已经不太热了,距离学校十几公里的海洋对我们这个北方的小城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每次老祁打开厚厚的棉絮下面冰桶的盖子的时候,凉气钻到我的每根头发丝中间,我都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仿佛电视广告里的男演员嗅到漂亮女孩的发香。「这傻小子......」老祁右手戴着粗线白手套,裸露的左手攥着一杯炒冰,手腕轻轻磕了我一下。「嘿,这味儿太好闻了!你再给我多装点呗。」我像往常一样装作没有看到他只有四根手指的左手,冲老祁挑了挑眉毛,笑得应该很谄媚。「小王八蛋,你自己看这还能装吗?都堆成山了。」的确,我随即一口咬下去,冰山少了大半截,我嘴里被冰得没了知觉,还是大叫「这回能装了!」老祁一勺子扣上来,我心满意足地从他手里接过被装得满满当当的塑料杯,把兜里的五毛钱扔进灰色冰桶前面的纸盒子里,嘿嘿一笑,扭头就走。我听见老祁在我身后呵呵笑了两声。不止我一人,几乎所有男生在老祁那买刨冰都耍这一套,老祁也从来不拒绝谁,嘴上骂我们所有人臭小子。大多数女生不好意思这样,但是我亲眼见老祁给女生装炒冰的时候压得特别瓷实,好像生怕卖不完化了。
2
有一天英语课,王权教我他新研究出的画骷髅头的方法,只要画一个倒三角的轮廓,两个洞代表眼睛,然后根据个人的喜好画上鼻孔和牙齿。「还挺像的......但是画出来有点像我们上周看的电影里的外星人啊」,我歪头小声跟他说。他轻描淡写地说:「你多练练找找感觉。」于是我低头努力练习,画了两页骷髅头,还准备继续搞点创作的时候,本子突然被抽走了,「Great!上课不听讲,在这画ET。」缪老师居高临下用眼睛斜着我,右手捏着满是各种款式的骷髅头这页纸,把本子抖地哗啦啦响。我赶紧低下头,瞟见小路在我旁边坐得笔直,也在斜眼瞅我。缪老师像收到了根本毫无兴趣的传单,轻蔑地扫了一眼我的本子,好像在确认那些滑稽的骷髅头跟小路没什么关系,就把我的本子甩到了地上,同时又瞪了我一眼。我惊异于她能同时做出那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情。缪老师转身往讲台走去,「李小平和王权上课画画,到最后一排站着去」。我懊恼地转头看小路,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妈过来了。「你又不是没被她逮着过,提醒你我也得挨骂」,我猜小路既不耐烦又怕事的轻声嘀咕传达的是这个意思。缪老师是小路的妈,但由于天性比较厉害且吃软不吃硬,和班主任老赵不太对付,竟然让孩子吃亏落得和我当同桌的下场。复述这话时小路的表情似笑非笑,我不太明白我是怎么能在老师之间的恩怨中插上一脚的,有一种被利用了的感觉。我和王权踢里趿拉地从狭窄的桌椅里挤出来,走到了教室最后,对视了一眼。「还不如让咱俩出去罚站,还能早点去找老祁买刨冰」,我小声说。「她咋知道是我教你画的?」听他发问,我指了指王权画满了骷髅头的手臂,再次相信了他大概真的有点傻。
「说到吃刨冰,你注意过老祁的手指头没?」
「看见了,没有大拇指!」
「你知道是咋弄的吗?」王权忽然变得有点神秘,我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要从他身后的阴影里跳出来似的。
「不知道,天生残疾?」「切,根本不是。他是年轻的时候好赌欠了很多钱,手指头被债主给剁了。」王权看上去很无所谓,好像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可我听到这句话感觉像是有一坨毛毛虫砸到了头上,赶紧用力甩了甩头。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他握着堆成山丘的刨冰杯子的手,干燥厚实的手掌连接着四根粗糙但称得上修长的手指,指甲干净——和我的比起来,因为并不丑陋,这只手尽管少了大拇指也没有那么骇人。
「你怎么知道?」「南山岭这样的人多着呢。」王权像第一次见我一样看了我一眼。
3
放学了,缪老师离开教室前还不忘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俩一顿,以「别让小路跟你们整这些歪门邪道」结尾。「悍妇。活该离婚。」我的肚子里翻腾了几下,脸上却抑制不住地发热,只能愤愤地想。缪老师在两年前离婚了,三年级开始学英语,我妈认为英语很重要,要好好巴结一下老师,于是让我找小路要来缪老师的手机号,打了一通长长的电话,希望她能多多照顾我,甚至带我一起登门拜访,拎了一箱牛奶和一条中华烟——结果家里并没有男主人。缪老师还是很豪爽地收下了烟,「我自己抽。」我妈觉得女老师抽烟是件很见不得人却又很值得宣传的事,有合适的机会便要拿出来讲,我却从没在缪老师身上闻到过烟味。我问过小路怎么从来没说过她爸妈离婚了,「我每天都能见着他俩,感觉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她说。也是,小路的爹老路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教体育,可以算得上高大威猛,体育课上并不怎么管我们,每次围着操场跑两圈之后马上就地解散,他有时候和我们一起打篮球,有一次把王权撞得摔到地上,整个右膝盖血淋淋的,老路赶紧把他背到医务室,我们几个男生在后面跟着跑,听见老路不断对王权道歉「对不起啊,老师不是故意的,跑得刹不住车了」。王权瘸了一个月,后来体育课上,路老师不怎么和我们一起玩了,常常坐在楼梯上抽烟,有时候不见踪影。王权有一次跟我说,老路撞到他身上的时候那股狠劲就像要跟他鱼死网破一样,根本不是什么不小心。他的胖脸上写满了愤怒和委屈,我白了他一眼,路老师跟你又没有仇,这么大个儿的人摔一下怎么了。至于缪老师和路老师两人为什么离婚,我妈好像没打听出来。尽管缪老师脾气大、离了婚还抽烟,我妈似乎还是对她有种莫名的好感,常常以打听我在学校表现为由给她打电话,缪老师也从不拒绝,两人聊上半小时是常有的事,而我在学校的表现在其中的比重少到让我妈忘记教训我,我也就很祝福她俩的友谊。这阵子我妈热衷于当红娘,常常给部队的年轻男女牵线搭桥,她的这份兴趣在缪老师身上也能得到释放,「女人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工作不容易,尤其是你当老师的,身体累就算了,心理负担也重,得赶紧找个人跟你作伴啊。」这种话我在我妈的电话前听过多次,要是现在还有接线员,估计都能把她的话倒背如流。缪老师似乎也没有拒绝我妈的意思,有一次我妈带上我去参加饭局,我一进门吓坏了。缪老师穿着在学校的公开课上穿过的一身西装套裙,头发上布满了非常有规律的、像小写字母a的卷。旁边坐着赵叔叔,是我爸的同事,前两年工作上出差出了车祸,他妻子当场身亡了,他面部挫伤,一条腿骨折,脑震荡,在医院躺了三个月。但是由于是公务出差而他私自带了家属,单位给的补偿很少。我记得我爸妈有一阵天天去医院看他,甚至有两天晚上都没有回家。再后来我妈和别人压低声音的闲聊里,那时候赵叔叔好像想自杀,于是院里各家轮流去看护、开导他,还特意派人回他南方老家把他父母接过来守着他,想自杀是绝不可能的。他看起来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除了右边脸颊上的一道极力想要隐身的伤疤。赵叔叔毕恭毕敬地坐在缪老师旁边,两个人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倒茶。我把这场景描述给小路听,她大发雷霆,把我的胳膊都掐紫了。
4
小路像往常一样,中午跟我和王权去买刨冰吃,还没走到老祁的小车前面,就看到他手忙脚乱地把烟灭了。「多给点儿,今天被缪老师罚了,气死我了。」王权很不忿。「缪老师?」
「是啊。怎么了?」
「没啥,感觉这个姓挺特别。英语老师?」「你怎么知道?」小路抢在我前面发问。「听你们之前说过。」
「你不知道缪老师还是她妈呢吧!」我用下巴朝小路的方向晃了下。「哟,是吗。当老师的孩子挺辛苦的吧?」小路低头没说话。「当那个母老虎的孩子当然辛苦了!」我抢着说。「你这孩子,不能这么说老师。」老祁竟然倒戈相向。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低头接过老祁托在手掌上的沙冰,「你怎么没有大拇指?」我脱口而出,立刻后悔了。
老祁怔了一下,我突然很怕他会哭。
「嗨,事故。」他的嗓子干干的。「哦,我就说嘛!」我松了一口气,仿佛看到他骨骼明确的断指处长出了一根新手指。「怎么?」我第一次在老祁那张长期保持笑容而制造出了几条自然的褶皱的脸上看到了疑惑的神态。「他!李小平说你是外星人所以只有四根手指!」王权突然大声说。我吓了一跳,比老祁更迷惑地扭头看王权。
老祁大笑,「这小子,太有想象力了。」
「你怎么乱说啊?我什么时候说他是外星人了!」我们仨打算一起去我家那个院子里的老防空洞「探险」,回去的路上我质问王权。「总不能让你说他是赌博被切了手指啊。」「那也是你说的,你肯定瞎编的吧。怕我跟老祁说了他揍你。」
「他也会揍人?」老祁虽然个子挺高,但是块头确实不大。尽管我们一直叫他老祁,他的实际年轻却也不得而知,看上去和我经常见到的中年人没有什么差别,如果用在学校刚刚学到的词语,也许可以说面容比我爸更「沧桑」一点。王权虽然跟我们一样四年级,但是年龄却要大三岁,吃得多又不爱动脑,膘肥体壮,仿佛能轻易把老祁那辆小三轮车掀个跟头。「我看,老祁的手真的有点像外星人。」我和王权争执的时候,小路忽然说。王权爆发出了一阵大笑。「而且,你真的告诉过他,我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见我摇头,小路的语气更肯定了。「那他是怎么知道的?谁会跟他说这种无聊的事?他一定是外星人才会知道这些!」我有点懵了,但还保持着一丝理智。「外星人......来我们这小地方卖刨冰?为啥?」虽然我认为我提出了一个笑话,但是王权竟不笑了,露出少有的思考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们疯了还是我太正常,和热衷研究外星人的朋友在一起我不思考外星人的存在是不现实的,我感觉我们正在打破某些界线,期待着天外来客的光临。
我们三人神色凝重地讨论了一路。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老祁把右手一直戴着的白手套摘掉了,那只手也缺少了拇指。我问他你是不是外星人,外星人才只有四根手指。老祁还是笑着,伸手把头顶的黑色鸭舌帽也摘了,露出了一个光滑的头顶,上面有两个可怖的触角。「你怎么长得不像ET?」我在梦里沉着冷静。老祁又呵呵呵地笑了:「外星人本来就不是那个样子。」第二天我起床晚了,飞奔出门,碰到了和我一样往学校跑去的王权。我抓住他的袖子说,老祁给我托梦了,他真的是外星人,并把通常都不会记得的梦境向王权复述了一遍。「他还有触角?看来是真的了......」我俩一起失魂落魄地进了教室,小路正趴在桌上看书。「别看了,」我把小路的书扒拉到一边,「老祁好像真的是外星人。」
5
我们决定去问老祁,他脾气很好,但是关于他是外星人这件事绝对是个秘密,就这样泄露了天机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们都难以想象。小路说,让老路陪我们去。「路老师怎么会对这种事感兴趣呢......」,王权看上去有意阻拦。我爸就喜欢这种怪事!不然也不会和我妈这种人结婚......小路仿佛很有信心,跑出了教室。下午有一节体育课,快下课的时候,小路真的拉着路老师过来叫我和王权。我俩很紧张,而路老师似乎也有什么难言之隐般眉头紧锁着。我们一起往东门方向走去,路老师一句话都没说,我觉得正常的老师都不应该在这种时刻沉默,于是说,让您跟我们一起干这种事感觉不太好。小路瞪了我一眼,她爸眉头皱得更紧了,「这也是我的事。」我和王权惊讶地对视一眼,没想到路老师也是外星人迷啊。我不再说话了,四个人气氛凝重地走出了校门。老祁正在抽烟,看见我们来了很高兴,「又被我逮着逃课出来买吃的.....」话没说完,大概看到了陌生的大人,他眼神里仿佛蒙上了迷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小路开口用那种上课回答问题的甜美嗓音说:「祁叔叔,我们觉得你可能是外星人,不敢确定,特意来问问你。」我紧张得攥紧了拳头,很怕她问出这句话,天上会忽然来一架UFO,把老祁,连同他的刨冰都一并吸走了。可是,老祁就好像没听到一样,直勾勾地看着老路,问:「路老师,您怎么来了?」我们仨站在这两人旁边面面相觑,我久违地在小路脸上看到了疑惑不解的童真表情,而我自己非常讨厌这种当小孩儿的感觉。路老师让我们先走,他有事要单独和老祁谈谈。我那时虽然是孩子,但是也意识到了路老师根本不是什么外星人爱好者。小路承认,她也根本不是这样告诉她爸的。「我在我家里见过老祁。我本来应该去上小提琴课,老师临时有事提前下课了,我到家的时候看见我妈和一个男的坐在沙发上,仔细一看竟然是老祁。我妈说让他来家里送点冰块。我从来没见过我妈喝任何不是从热水壶里倒的水,而且老祁临走把你妈带来的中华烟给他带上了。我告诉我爸了,我爸说他可能知道那是谁,我让他跟我来看看。没想到,他们真的认识。」我和王权为了防止小路跟着,还有十分钟放学的时候就溜出学校了。可是老祁已经不在那了。「他和老路抢缪老师,现在找个地方单挑去了。」王权很确信。缪老师竟然这么抢手,我实在不愿意相信,毕竟赵叔叔在缪老师的殷切招呼下都没有再跟我妈提过这事。但是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要不去你们村找找他吧!」
6
虽然叫南山岭,但实际上是个虚张声势的名字,南山岭没有山,只有几个土丘,土丘上有青灰色的草皮,下面则堆满了垃圾,旁边有几乎可以称得上连绵的十几排平房。每排的排头排尾各有几棵柳树。我从没见过在盛夏时节还这样光秃灰暗的柳树,没有随风摇曳的嫩绿的枝丫,仿佛长在这里的树都比河边的柳树生活艰苦。所有房子的屋顶都铺着蓝色瓦楞,有些似乎为了防漏水加了几层,用石头压住,本就矮小的平房看起来不堪重负般长满了裂痕。除了每家每户门的材质和颜色略有不同以及门外晾的衣服在主人看来有辨识度,这些房子基本上是千篇一律。尽管南山岭就在我们院旁边,但我还是第一次走进来。王权也不知道老祁住哪间房,据说他从没在村里碰见过老祁。我们漫无目的地在房屋的间隔里穿梭寻找,发现老祁的三轮车停在最里面那排房子前的柳树下。我们跑过去,没人。但是有一件房门口摆着一台隆隆作响的机器,我以为是谁家的洗衣机在洗衣服,王权却拽着我走过去,「不像洗衣机,感觉是冰柜!」我一下紧张起来,和王权一起蹑手蹑脚靠近那台可疑的机器。果然,西瓜味的冰桶就在后面,这是老祁的冰柜!冰柜旁边的门紧闭着,但是大开的窗户传出了老祁说话的声音。我和王权屏住呼吸,蹲在窗户下面。「当初苗苗给我写信说要和你结婚,其实我松了一口气,我当然希望你们过得好,可是你对她动了粗,按她的性格,肯定要和你闹离婚。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承认我回来是还想着她,但是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只能偶尔去看看她,别的也不想了。没能走到一起,是我命不好,我们没有缘分。」路老师的声音响起,王权冷不丁打了个寒颤。「那件事是我不对,也没指望她能原谅我。她现在经常去相亲,你知道吗?就那个整天去找你吃刨冰的李小平他妈,喜欢干这种牵线搭桥的事儿。」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伤感,我也因为突然被提起大名儿吓了一跳。「我知道。」老祁的声音很平静,「她要能再找个部队的,条件比你也强多了,就是你女儿,心里不定多难受呢。」我想到了小路下午对我们讲那段话时的眼神,有点茫然,有点不解,语气却满是不在乎。「她啊......有什么事她也不跟我说,也不跟她妈说,整天和几个小男生疯玩。当父母真难啊,自己的事都管不好,经济条件也不怎么样。她妈毕竟还是英语老师,能辅导功课,我是个体育老师,小时候陪她跑来跑去还行,现在大了,除了跟孩子说几句自己都不信的大道理,别的什么都教不了她。我们对不起这孩子啊。」「也别这么说,我看你孩子跟你挺亲的,就去你家一会,被孩子看见了,不是立马转头就通知你了吗......」屋里沉默了一会。路老师说:「咱俩能这么聊聊挺好,疙瘩都解开了。我不打扰你了,以后多聊聊。」我和王权各自沉浸在偷听的对话带来的震惊里,一晃神,门已经开了。路老师走出来,看见了我们准备逃跑的姿势。看躲不掉,我俩也就松软下来,哐当坐在了地上。「小路没跟着你们过来?」我摇摇头,路老师走了。老祁听声音出了门,看见我俩呆坐着,没说话,转身从屋里拿了两个杯子出来,打开他的冰桶,装了满满两杯刨冰递给我们。我盯着他的右手,为了缓解尴尬而口不择言:「你还没回答小路的问题呢。」「什么问题?」他愣住了。我本想说算了。他忽然开口了。「外星人是吧?我怎么可能是外星人。我这手啊,是工伤。」说着把脱去手套的右手在我面前挥了挥,五根手指都健在。「我不是外星人,让你们失望了。但是我见过外星人。我见过的那个外星人啊,真的只有四根手指头,我看着还挺亲切的。就在后面土丘看见的,我三轮车旁边的柳树那,看见没,它就是从那消失了的。你们和我一起在这等等,说不定它会再来的。」
7
外星人?我不是,但我可能见过。不是在火车行驶过的一片荒野或者开阔的浅滩,甚至不是在电影里那样的深夜里。一天早晨,我去菜市场买西瓜回来,村民都出去打工了,南山岭很安静的,我抱着一个大西瓜,手里还拎着几包白砂糖和中午我要吃的蔬菜。我走到两排房子中间的被看作南山岭的分隔符的土丘时,忽然觉得微风吹来,在夏天的上午舒服极了。随后我看到一个光溜溜的「人」在那一小片杂乱的空地上,跳舞。说它是人,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有头、四肢,但是那颗头颅很小,四肢很长,跳舞的样子像风吹过的柳树。不是我们城市里被晒得蔫嗒嗒的那种,而是夏天的西湖边上,成排的、光洁、湿润,风一吹就柔柔地摇摆起来的一棵柳树。我抱着一个大西瓜,看着那个外星人跳着一种流动的舞的样子,脑子里忽然浮现出苗苗以前跟我一起去游泳的样子,她在水里像一条小金鱼,手脚没什么大动作,但是却安静飞快地向前游去。好像随时都可以从我身边悄悄流走一样,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抓不住她的。我一定是发怔了,人在这种时候都很醒目的,和你在课堂上走神总能被老师发现一样。那个「人」发现灵魂四处游走的我了,它停止跳舞,一双乌黑的亮晶晶的眼睛看向我,我看不懂它的表情,如果以人类的解读方式,它的眼神一定是在诉说恐惧。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不知道它会对我做什么,也不知道我要跟它说点什么。如果我今天早点起床,也许这会儿已经用那台和削去了我的手指的机器差不多的刨冰机做好了刨冰,那我就可以请它吃上一杯,像我每天都在做的那样,也许能顺利赢得它的好感。可惜,它向着与我相反的方向快速离去了,它走路也是柔柔的,像是一团被揉捏得恰到好处的云。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于是就像我一直以来习惯的那样,像苗苗走的时候,包括后来我的几个女朋友走的时候那样,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注视着它走了。它走了大概一百米,忽然转过身,冲我挥了挥手,它的胳膊那样修长,我又感受到了一阵有海水气息的微风。我长到这个年纪,没有什么本事,只有视力极佳,还没受伤的时候参加过飞行员的测试,视力2.0,可惜有色弱,没能成为飞行员。后来没多久我就负了工伤,也就没那么不甘心了。我看到它和我一样,挥舞着的右手上只有四根手指。它还是走了,我呆站了一会也回去了。我从门口的冰柜抱出昨天冻上的冰块,开始准备刨冰。一会儿,我就要骑着那辆破三轮车,驮着一桶刨冰去小学东门,只是为了去看看苗苗的孩子,那个曾经有可能属于我的孩子。
本文为人物【像小说家一样写作】系列课程双雪涛学员优秀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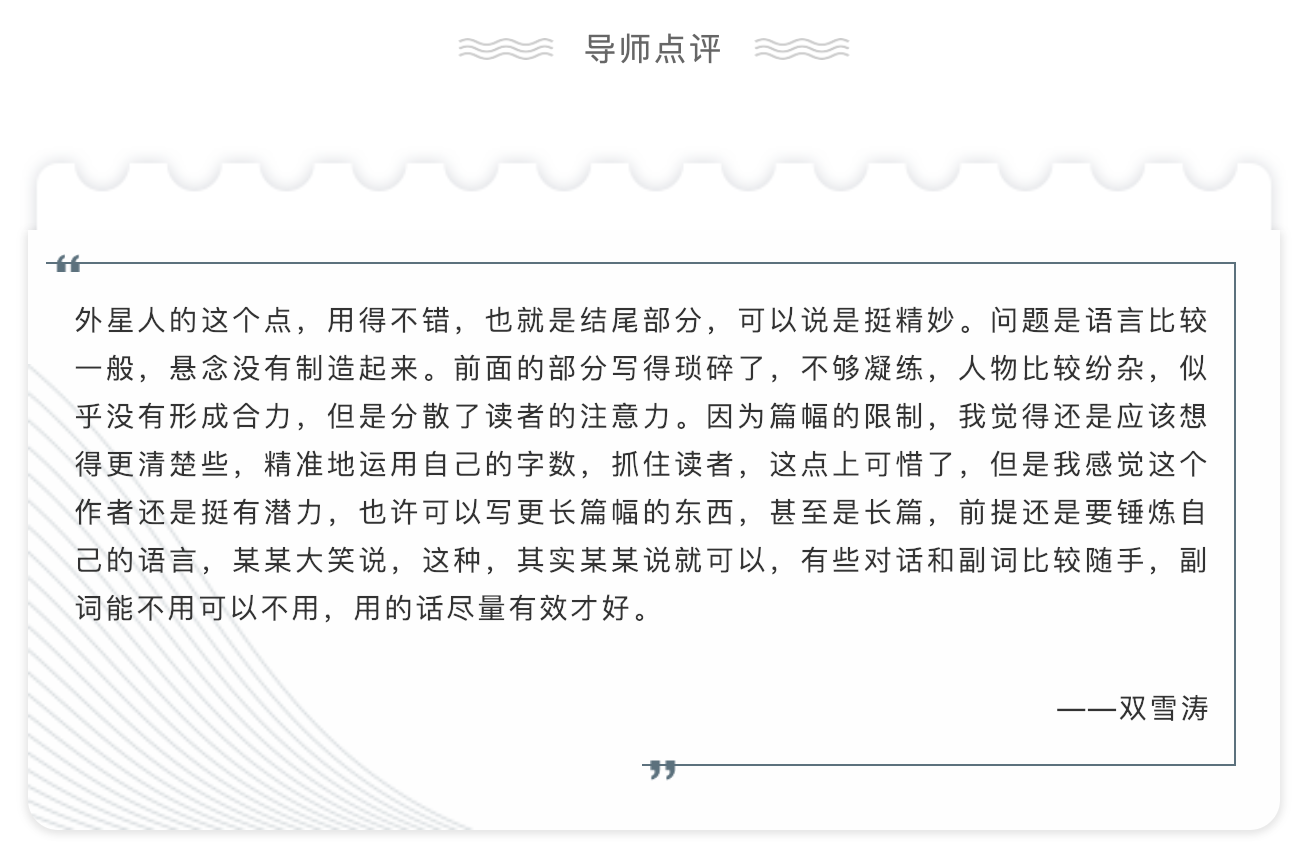
两个月前,我们联合了双雪涛、笛安、郝景芳 三位优秀青年小说家打造了写作课——《像小说家一样写作》,90天的精心打磨,3位小说家首度系统公开的36节写作课程,《像小说家一样写作》会让你了解小说究竟是什么,如何去搭建小说的世界,如何赋予人物生命。
TOP STORIES
相 关 推 荐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624号